科幻文学在新颖的叙述形式中仍然保有其思辨性,是时代文艺转型的助力。
主持人语:
新大众文艺和科幻文学究竟有何关系?当我看到困在算法和大数据里的外卖员写出诗集《赶时间的人》,我忽然意识到:世界早就变得无比“科幻”,而置身于科幻和现实边界地带的芸芸大众,不论是投身创作还是选择阅读或观看,都成了新大众文艺的切实参与者。更何况,科幻文学本不“小众”,它在诞生之初即怀有面向大众的抱负。本期邀请四位青年评论家、作家参与讨论,他们对新大众文艺和科幻文学的历史与当下、生产与传播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张鑫(《钟山》杂志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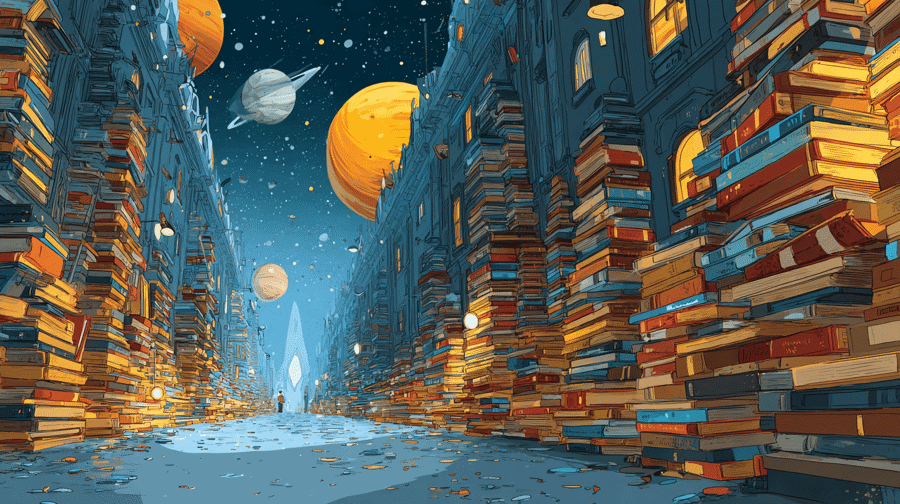
“高概念”最终要落在现实土壤上
对写作者而言,科幻创作更像是对现实的重新编码,用新的观念体系包装旧的世界,又在这一基础上保留足够的情感锚点,以陌生化的手法重新制造伦理叙事的突破口。这里涉及了科幻的两种类型,即硬科幻和软科幻。硬科幻对作者本身的专业背景有一定的要求,所创建的科学细节也更经得起细究。而日渐流行的软科幻则将重点放在社会科学和人文表达上,以一种更类现实的面目出现。从纯文学转而创作科幻的作家大多选择后者,让家庭、恋人、朋友等多对情感关系参与其中。小说仍然紧扣伦理矛盾,但抛弃陈旧的琐碎叙事,挖掘出了全新的表达方式。某种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纯文学的科幻演绎,只是用幻想的外壳包装了沉重的内核。这类创作对作者的知识背景要求相对较低,小说的思辨性要更强于故事性,目的同样在于引起情感共振。文本对现实进行陌生化处理,使其反思性不再受到外界因素影响,不加掩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然而,概念先行是诸多科幻小说不得不面对的弊病。在创作过程中,如果幻想占比过多,作者就会陷入叙事细节不足以支撑构想的窘境。如何在空中楼阁上架构出经典的思想困境,成为科幻写作者的切实问题。困境与现实相连,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小说的文学性。相较于现实主义作品,科幻写作建立在想象之上。但这并非代表科幻真正跳出了世界的局限,因为人们无法彻底脱离现实,故事必然处处受制于作者的基础认知。哪怕是颠覆惯常世界观的作品,也往往在其他方面显示出与现实丝丝缕缕的关系。作者找到了现实与幻想间的空隙,必须平衡两者的参与度,才能让某些难言的情感得到清晰的表述。读者依托现实对新世界进行解码,能够抛开自己的观念禁锢,重新认识同一问题的多个位面。
科幻作者创造“高概念”的世界观,但需要以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其“落地”过程囊括了多种类型的结构方式,最终得以探讨更深层次的对象。当下最主流的结构就是时间与空间的杂糅,为读者创造出供以思考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叙事时间被打乱,故事发生的空间也不一定拘于现实。天瑞说符的《我们生活在南京》构建了一方典型的空间折叠。小说讲述当下和未来两个时空下的南京,主人公采用无线电作为媒介进行交流。双线结构使故事更为清晰,在拯救未来的宏大命题中加以叙述少男少女跨越时空的感情。这部作品首发于起点中文网,后续还会进行影视转化。当下,新媒介已然重塑了多数人的阅读形式,科幻小说在网络平台上的占比较大,影视改编后可能带来的影响力则会进一步扩大。人们更活跃于类似的文学与影视平台,是大众参与文艺活动的表现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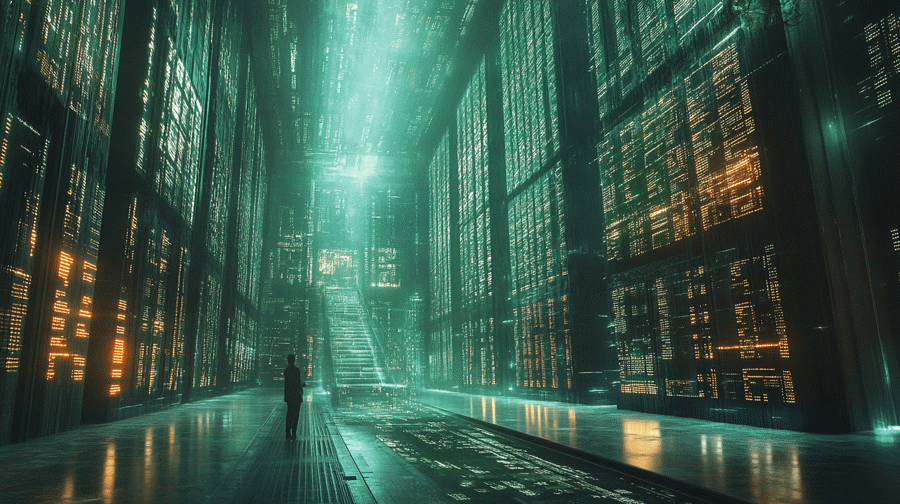
在新大众文艺繁盛的今天,科幻文学给当代文坛注入了新的能量,或许正是求变的契机。对未来的幻想消解了纯文学的严肃性,承载科幻文学的多种媒介也论证了人们对通俗文学的取向,大众对这类创作来说不再是抽象的假想符号。科幻文学成为更多人想象的载体,也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叩问历史。它往往填充大量想象的细节,使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作品中实现平衡。面对过去的矛盾,未来怎样改善或是如何爆发,成为小说里值得关注的焦点。
以陈楸帆的创作为例。《荒潮》构建的硅屿岛写到了潮汕宗族文化和普度仪式等民俗元素,与赛博格改造、病毒危机元素结合在一起,在保有历史性的同时,实现了现实与想象的结合。他在今年推出的新作《刹海》选择了环境灾变的主题,小说里讲述地球因气候变化濒临崩溃: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资源枯竭、物种灭绝,人类文明面临存亡危机。生态问题在这类的科幻小说中彻底爆发,人与环境的关系成为具有历史性质的议题,让居于当下的读者开始反思。
新大众文艺让主流文学的精英感逐渐褪去,科幻文学在新颖的叙述形式中仍然保有其思辨性,是时代文艺转型的助力。从本质上来说,科幻创作就是在伦理困境之上建立虚幻王国的过程。作者对世界进行编码,读者在经验的基础上完成解码。最终呈现在面前的,是抽离外界环境后的经典议题。创作者采用多种方式让“高概念”实现落地,最终都深入了现实的土壤。
阅读原文
作者丨朱霄(青年作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来源丨上观新闻
编辑丨王越月
编审丨戴琪
更多阅读:
文汇报丨新大众文艺与当下的科幻文学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