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地理学自地理大发现时代兴起,从西方殖民探险与扩张中孕育科学萌芽,逐步发展为承载国家意志的“爱国科学”。从拉采尔的“生存空间”理论到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从航海技术到地理空间技术,地理学家通过构建空间认知范式与技术体系,不仅支撑大国竞争,更以知识权力重塑全球格局。
在当今大国博弈复杂的背景下,回顾地理学与大国竞争的发展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更清醒地认知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地理逻辑与权力密码。

[美]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冰山》(18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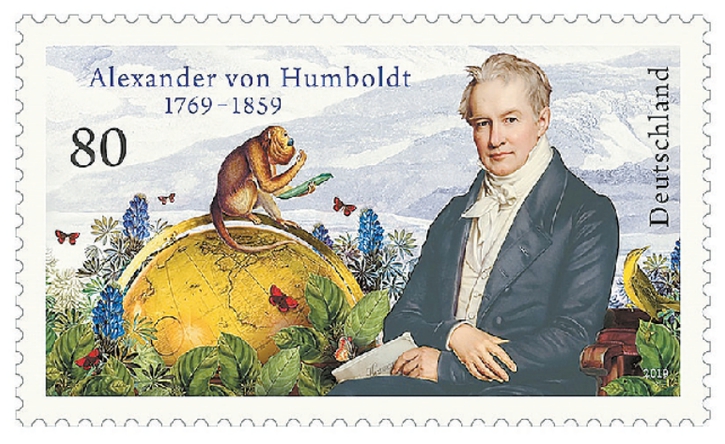
2019年德国发行“亚历山大·冯·洪堡诞辰250年”纪念邮票
现代地理学:起源于大国竞争
地理学,这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与人文现象空间分布规律的科学,其诞生和发展与大国间的权力博弈密不可分。“地理学”(Geography)一词源自拉丁语,意为“对地球的描述”。然而,这种描述并非纯粹客观的记录,而是人类组织、占领和管理空间的动态过程,是权力与知识交织的产物。
早在古希腊、古罗马、古代中国和阿拉伯帝国时期,地理知识便已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工具。对地形的考察、气象的辨识、方向的指南等实用地理知识,直接服务于军事征服与疆域管理。这些分散于各文明的地理探索,虽未形成系统学科,却无不受到国家权力中枢的驱使。古罗马军队的行军地图、中国汉代的西域勘测、阿拉伯帝国的航海指南,都是地理知识服务于政治实践的体现。
15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大国竞争的全球时代。哥伦布寻找东方航线的计划,正是在葡萄牙与西班牙海上争霸的背景下获得支持。1492年西班牙资助其西航,旨在打破葡萄牙对东方贸易的垄断。这场由竞争驱动的航海探险,不仅发现新大陆,也催生了现代地理学的萌芽。
17世纪航海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推动了探险活动的发展,地理学逐渐从“导航之学”发展为“探险之学”。1769年,库克船长(James Cook,1728—1779)首次驶入太平洋,被视为现代地理学的重要转折点。因为这次探险有着特别的科学目标,是在一批杰出的国际专家陪同下完成的,它标志着地理学从帝国扩张的工具,逐步转向以科学探索为核心的学科范式。库克用三次航行的亲身实践,在以前探险家的基础上绘制出了世界地图的基本轮廓。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地理学进入建制化阶段。1788年法国成立非洲内陆促进协会,随后德国、英国、俄国等相继建立地理学会。成立于1830年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更成为全球探险的核心组织。这些机构不仅是学术平台,也是殖民扩张的策源地。它们通过系统测绘、资源勘探,为欧洲列强的军事与商业扩张铺路。
随着对世界特别是新大陆地理知识的积累,欧洲大学陆续开设地理学专业课程,内容涵盖地图绘制、航海术等。地理学因其在国家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被塑造为“爱国科学”。德国在大学改革中提升其地位,法国则将地理教育作为培养民族认同的途径。至19世纪中期,地理学已成为欧洲学校的必修课,强化了学生对国家疆域和世界的认知。
在西方地理探险与殖民扩张中,涌现出大批杰出的地理学家,其中包括德国地理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洪堡通过广泛的全球考察,揭示自然要素间的因果关系,建立起整体性地理观,推动了地理学从经验描述向科学规律探索的转变,被誉为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然而,洪堡的研究仍依赖于殖民体系所提供的全球通道,其知识生产难以摆脱帝国视野的烙印。
地理科学理论:大国竞争的战略先声
19世纪末,欧洲列强扩张达至顶峰,地理学跃升为“帝国科学”,成为支撑殖民体系的重要知识体系。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和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分别从国家动力与全球海陆结构两个维度构建了现代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基础。他们不仅解析世界自然和人文现象,更直接服务于殖民扩张,其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西方大国竞争策略,遗留思想仍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产生回响。
拉采尔:“生存空间”理论与大国竞争的动力源泉
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的学术思想与德意志帝国崛起进程深度交织,其理论体系既映射着国家统一的澎湃动力,更暗藏对生存空间的深层焦虑。普法战争的从军经历与1871年德意志统一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他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进而驱使其为亟待“争夺阳光之地”的新兴帝国构建扩张理论。
拉采尔的创新在于将生物进化论引入政治地理学。他通过《人类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等著作提出“国家有机体”理论:国家如同生命体,需通过领土扩张满足生存发展需求,边界应随国力强弱动态调整。由此推导出著名的“生存空间论”——地球有限空间下的资源争夺,必然引发国家间冲突,唯有持续扩张的民族方可维系强盛。这种以生物学隐喻包装的“科学法则”,实则为大国竞争提供了一套暴力合理化逻辑。
这套理论精准嵌入德皇威廉二世的全球战略框架。拉采尔不仅论证了德国扩张的“自然合法性”,更提出两项战略路径:其一是在欧洲打造以德国为核心的“中欧大空间”,凝聚日耳曼力量形成战略实体;其二是仿效马汉海权论,主张扩建海军争夺全球海洋霸权,突破英法等传统殖民帝国的地缘封锁。
拉采尔学说的历史宿命在于理论工具化。尽管他主张适度扩张,但“生存空间”概念被后继者极端化: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1869—1946)等地缘战略家将有机体理论升级为“生存权战争”学说,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1849—1930)等军国主义者更宣称“武力拓展空间是自然法则”。这些变异思想最终沦为纳粹“种族生存空间”论的理论基石,使拉采尔的学术遗产蒙上深重阴影。他的地缘政治框架虽开创了学科范式,却也因暗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成为20世纪人类灾难的思想催化剂。这种科学理性与帝国野心的复杂纠缠,至今仍警示着学术与权力的危险共生关系。
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与大国竞争的战略图谱
当拉采尔为大国竞争注入“生物性动力”时,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正以空间范式重构全球战略格局。1904年,他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划定的理论坐标,至今仍是地缘政治的经纬主线。
麦金德将欧亚大陆内陆腹地2300万平方公里区域定义为“心脏地带”——这片马背上的土地因河流内向、缺乏不冻港而天然排斥海权力量。他预见铁路技术将激活大陆力量,使控制“心脏地带”的陆权国家(当时指俄国或德国)获得重构世界秩序的潜能。其著名的战略三段论将地缘政治简化为空间控制链:“东欧-心脏地带-世界岛-全世界”,这为海权国家敲响双重警钟:既要防止“边缘地带”被陆权渗透,又需阻断“心脏地带”形成统一力量。
两次世界大战成为麦金德理论的试炼场。1914年德俄对东欧的争夺印证了其初始判断,1919年巴黎和会上,麦金德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将其理论转化为具体策略:肢解中欧、阻隔陆权联盟,为大英帝国设计出“大陆均势+海洋独占”的双重安全阀。至二战后期,麦金德提出“环形防线”(米德兰洋)概念,主张以北大西洋作为战略核心,整合法国、英国与北美力量组建跨大西洋联盟,以此实现对“心脏地带”的战略包围。这一前瞻性的构想,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正式成立埋下了重要伏笔。
麦金德的理论遗产并未随大英帝国衰落而消失,反而被新兴大国——美国完整承袭。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1893—1943)1942年提出“边缘地带论”,将麦金德命题倒置为“谁控制边缘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为冷战初期美国“新月形包围圈”奠定基础。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1928—2017)则在《大棋局》中将心脏地带具象化为“欧亚巴尔干”,其肢解苏联的战略与麦金德割裂大陆的构想形成世纪回响。当前美国的印太战略布局,本质仍是“边缘地带”理论的现代复刻:通过“四边机制”构筑海上长城,在数字技术时代延续陆海对抗的古典逻辑。
作为海权文明的自卫宣言,麦金德的理论揭示了地缘政治的本质矛盾:海洋国家对于大陆整合的本能恐惧。从大英帝国到美利坚霸权,对“心脏地带统合者”的想象始终是海权力量的战略梦魇。这种恐惧驱动的遏制逻辑,既造就了20世纪的地缘断层线,也持续塑造着数字时代的新型铁幕。当陆海对抗从地理空间延伸至网络、太空等新域时,麦金德的理论幽灵仍在寻找新的宿主。
拉采尔的“生存空间”理论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是现代地理科学介入大国竞争的两大支柱。前者为西方大国扩张提供“科学”依据,后者绘制了遏制与反扩张的战略地图。它们表明西方地理学从未脱离权力政治,既是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也是服务大国竞争的战略工具。这些理论开创的地缘政治思想,已融入西方大国战略基因,成为其审视全球、谋划竞争的先声。
地理科学技术:大国竞争的底层重塑者
地理科学不仅是探索世界的钥匙,更是大国博弈中的战略利器。自19世纪精密测绘技术兴起,历经冷战卫星遥感时代,直至数字时代的地理人工智能(GeoAI),地理科技的每一次革新都深刻影响着大国竞争的底层逻辑,推动其从理论到实践发生革命性变化。
军事战略:地理技术的深度嵌入
地理科学技术与国家战略能力的提升紧密相连。古代,航海、勘测与地图技术是战争的重要指南;现代,地理信息的战略价值更加凸显。二战中,诺曼底登陆的成功,离不开精确的潮汐测绘;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全球首套立体地形分析系统应运而生。主要参战国纷纷建立大规模测绘体系,将地图情报系统纳入作战链条,地理技术正式成为国家战争机器的核心组件。
冷战时期,美苏争霸推动了遥感侦察与空间分析技术的飞跃。美国“日冕计划”构建了完整的遥感技术链,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航拍图像精准识别苏联导弹阵地,验证了遥感技术在核危机决策中的关键作用。随着卫星监控网络的形成,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成为模拟作战环境、规划后勤线路、整合多源情报的重要工具。GIS与GPS的融合,催生了“地理坐标—位置识别—导弹制导”一体化打击体系,并在海湾战争中得到实战验证。
资源控制:地理技术的空间赋权
冷战结束后,大国博弈的主战场转向资源版图。石油、稀土等战略性资源的空间分布与获取路径,成为国家安全与区域稳定的核心变量。地理信息技术由服务战争部署的“空间赋能工具”,转化为服务于资源主权主张、环境监测与海外利益拓展的“空间赋权平台”。
极地地区是地理信息技术发挥关键作用的典型区域。北极国家通过高分遥感测绘、重力异常分析与GIS地貌建模,构建支持其“自然延伸大陆架”主张的科学证据。深海资源勘探同样依赖高精度海底测绘与三维GIS建模系统,各国通过海底高分辨率地形图与三维地貌重建,强化资源空间的战略识别与控制能力。
数字主导:算法时代的地理空间战略
进入21世纪,地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融合深度学习、知识图谱与数字孪生,重构了地理空间信息的组织方式与表达逻辑。数字时代的版图争夺转向对地理数据标准与空间叙事的主导,技术规则成为大国较量的新战场。
全球范围内,地图平台之间的标准之争愈演愈烈。美国Google Earth Engine凭借成熟的API体系与算法模型,成为全球遥感分析的“事实标准”;欧盟Copernicus推动成员国间的数据接口规范接轨;中国通过“天地图”等平台构建自主技术体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认知网络。技术标准背后蕴含着制度权力,地图标签、数据模型与平台规则成为全球认知秩序的关键变量。
当前各国正加速构建面向战略需求的地理空间智能系统。美国“认知地理情报”战略旨在构建数字时代的战略沙盘,提升其在全球军事部署与态势研判中的响应能力。AI算法正在重构“战略资源的价值权重”和“主权边界的数字形态”,赋予技术领先国“空间叙事”的建构权,同时加剧国际社会的信息不对称。掌握地理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国家,实质上控制了空间数据的解析逻辑,地理空间智能系统正在成为重塑国际秩序的战略性工具。
从军事战场的数字化指挥,到资源争夺的空间赋权,再到算法时代的标准制定,地理科学技术不断突破传统边界,持续重塑着大国竞争的底层逻辑。在技术迭代与战略需求的互动中,地理科学技术不仅改变着国家权力的投射方式,更深刻地影响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走向。
新时代:中国地理学的新使命
纵观数百年大国竞争历程,地理学以其独特的空间视角,持续为国际战略博弈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从拉采尔的“生存空间”理论,到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再到当今地理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战略体系,地理学在大国竞争中的关键作用日益凸显。当前,世界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治理开辟了新路径,也为新时代中国地理学赋予了从理论重构到实践创新的重要使命。
新时代对中国地理学提出了更高要求,亟需实现从理论体系到实践路径的全面创新。在理论层面,应推动根本性突破,超越传统地缘政治中的零和博弈思维,构建以共生为核心的新范式。既要立足经典地缘理论,深入解析全球变化与区域冲突的地理机制,也要将“心脏地带”概念拓展为连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纽带,将“生存空间”的竞争逻辑转化为“共生空间”的合作框架,为全球治理提供理论指引。在实践层面,需要加强以地理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尖端地理技术的发展与运用,汇聚与融合多源地理信息数据,构建能够精准映照现实的全球地理大数据平台与数字孪生系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与决策支持。同时,要深化区域国别地理研究,聚焦大国博弈关键区域和“一带一路”重要节点,促进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深度融合,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地理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与理论建构。
新时代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不仅关乎学科自身发展,更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贡献。我们应把握时代机遇,推动地理学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深入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共同谱写和平、美丽世界建设的新篇章。
阅读原文
作者丨杜德斌(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地球科学学部主任,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来源丨文汇报
编辑丨王蓝萱
编审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