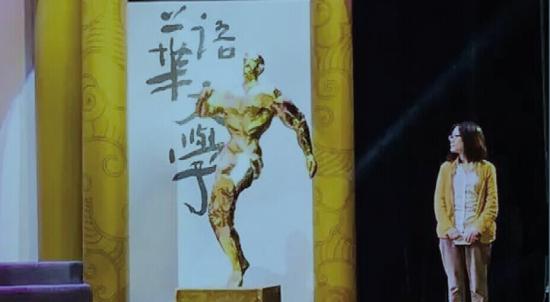

25日下午,由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正式揭晓,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作家毛尖凭借作品《有一只老虎在浴室》获得“二〇一四年度散文家”。
毛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专栏作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学士,中文系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研究涉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电影,世界电影和英美文学。着有《非常罪,非常美》、《没有你不行,有你也不行》、《乱来》、《这些年》、《有一只老虎在浴室》、《一直不松手》等,译有《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授奖辞
毛尖的文章短小精悍,趣味盎然,语藏机锋,下笔果决,纸上的纵横捭阖,呼应的往往是现实的狂欢。她将学识隐于幽默,尖锐见诸笔端,不卖弄,真赤诚。她出版于二〇一四年度的《有一只老虎在浴室》,纵论电影、世相,反应敏捷,角度新异,不避俗词,不责俗趣,那些灵光一现的神思,如同她灵巧、智慧的语言,总能直入所论对象的内部,坦荡直言但无诛心之论,语义凛然但也不失好玩之心。她以专栏名世,却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散文写作的类型。
获奖感言
很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被别人称为专栏作家的时候,老实说,我内心有一种抗议,干嘛要加个前缀呢!所以我很努力地写啊写,上门女婿一样希望获得丈母娘的欢心,盼望早日摘帽直接成为“作家”。这种心思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不太确切,反正,这几年,我越来越愿意以专栏作家的身份站在我的位置上。
回忆起来,我年轻的时候,所有的文学偶像都是写长篇的,无论是曹雪芹还是托尔斯泰,无论是金庸还是钱德勒,他们无一例外是写小说的,搞得我也一直神叨叨地以为将来我是要写小说的。但我现在完全不这么想了。
几年前,我的导师王晓明召集我们十来个学生去崇明,讨论在这个平庸的时代如何作为。当时,我们把未来的计划命名为“热风”,沿用的,自然是鲁迅的说法,“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那天晚上,刚好碰上台风,屋外地动山摇,我们在里面也心动旌摇,摩拳擦掌地准备给这个寒冽的社会送上有温度的批评。说老实话,后来我们没有做得多好,但是,那个晚上的热烈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在彼此的激情和愤怒中辨认出一种休戚与共感,虽然大家都差不多人到中年,但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热情让我们很容易就冲动起来。那些来自我们成长年代的高尚愿望,那些被今天的生活所屏蔽掉的很多词汇,如果还能感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感动更年轻的人呢?像“见义勇为”这样的行为,即使在今天不再构成我们生活的本能,但至少,我们可以在写作中恢复它,首先把它变成一种语词的本能,然后让它继续生长。用诗人兰波的话说,只要我们按捺住焦急的心情,到黎明时我们定能进入那壮丽的城池。
这就是我理解的专栏的使命,在今天,它的纲领一点不逊于小说,专栏作家在这个凛冽的时代当有更大的作为。世界再大,没有专栏作家不能登陆的地方;道路再窄,没有专栏作家不能插足的可能。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比诗人和小说家更草根更率性更自由,我们没有过多的历史负担,也没有操不完心的排行榜,我们可以是一线的文化清道夫,一个转身,我们也可以是深闺的八卦爱好者。本质上,我们与万事万物有着更家常的潜在情义,我们是通俗世界的一部分,是这个平庸的时代造就了我们,而我们全部的工作,就是改变这种平庸,直到时代最终把我们抛弃。
对写专栏有蛮大的敬畏感
南都:首先恭喜你获得今年的华语文学散文家奖。得知这个消息时,有些什么感受?
毛尖:老实说,挺高兴!因为尤其像我是专栏作家,突然拿到一个散文家奖,还是会感觉很意外,类似同性恋一夜之间得到社会认可,专栏作家也能摘掉前缀算“作家”了。(笑)另外一个呢,也是因为平时很少有人会用散文家来形容我,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散文家。
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也还是很不安的,因为有赵园老师、沈昌文先生在今年的散文家奖提名里。我很喜欢赵老师,她是我们读书时候的偶像,人和文章都好;沈先生的文章也是,老而弥坚,老而弥欢。所以,我是觉得自己还没到那个份上,这也是真实的。
南都:你曾说过,“专栏作家”就像男女朋友一样,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不能登堂入室。那现在得到这样一个文学奖的认可,有些什么想法?
毛尖:我还是蛮感谢南都的,这是对我们专栏作家的一个极大肯定,尤其我还算是一个左派专栏作家。
南都:什么时候开始写专栏的?有没有什么契机?
毛尖:那是2000年,当时的《万象》掌门陆灏应香港信报老板林行止先生之约,在《信报》上开一个“上海通信”专栏,陆灏就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写。那时,我从香港修完博士课程,拿到博士候选人资格回到上海,正准备博士论文。岁月苦长,专栏苦短,就开始了。自己当时很有些自以为是,觉得写个专栏,小菜一碟的事情,后来才知道岁月苦短,专栏苦长。
当然,说起来,在这之前,年纪更小的时候也写过一些小文章,但是正式写专栏,有规律地、半职业化地写专栏,是从2000年开始的。
南都:你是如何做到,自己的文字可以和不同年龄层次甚至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对接?
毛尖:谢谢你的赞美。硬说的话,也许和我从小在大家庭生活的经历有关。18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宁波,在外婆家长大,那时家里很多人,老的、壮的、少的,而且外婆家大门不到天黑也不会关,天天傍晚很多邻居来串门,这个大概养成了我和不同人交往的兴趣和能力吧。说起来,散文就是生活经验的结果,你说我可以和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对接,本质上,估计是我比较有能力和不同的人交往和聊天,这是一种生活经验,后来变成了我的写作。
南都:董桥在《有一只老虎在浴室》的序言里称赞说,你没有写不出文章的这层烦恼,说你心手机灵,要风要雨都不难。事实如此?
毛尖:这个肯定不是啦,这是董先生在嘲笑我。刚开始写专栏时,年轻气盛,自觉下笔泉涌,吹牛说一天七篇专栏都没有问题,估计董先生就是笑的这个。当然,很快,一年都不到,我就开始感觉专栏没有那么容易写,明明生活有限,却要做到专栏无限的样子,所以,常常也有装神弄鬼的时刻。说到底,能像董先生保持那样的频率、篇幅的写作,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南都:你的专栏写作持续了也快16年了,这中间有没有瓶颈?
毛尖:其实比起那些写了一辈子的作家,我真是专龄不长的。我还记得最早在《信报》写专栏,我左邻右舍的专栏作家常常就有写了半个世纪的,有的,写着写着去世了。不过,我现在专栏写了十五六年,整体已经感觉有些疲惫,你要说瓶颈,现在就是瓶颈,类似阳痿的感觉。尤其到了中年,那种靠青春、靠热情写作的阶段已经过去,但中年人的阅历又还不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似的。所以我蛮想休息一段时间,用流行的话来说,世界那么大,我得去玩玩。如此,得这个奖对我来说,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说,倒也有点尴尬,我接下来也不好意思不写吧,毕竟不是终身成就奖。(笑)南都:真的会去休息?
毛尖:我当然希望会有一个比较长的休整期,比如两三年,甚至五年。写专栏是一个消耗的过程,我需要再积蓄能量再出发。另外,我自己也感受到,我这几年的想法也有很多变化,所以更希望能静下心来休整一段时间。
这样的愿望其实也存在心里好久了。不太可能马上实现。一方面很多约稿来自朋友,也不好意思打退堂鼓;另一方面,我也说自己手贱,常忍不住想发表意见。用我妈的话说,退休以后的工作热情,自己也会吓一跳。
南都:现阶段,哪些东西始终是你想要表达、不写不快的?
毛尖:我现在蛮自觉把影视剧批评作为我的专业,看到烂片就像看到蚊子一样,忍不住要伸手。当然,看到好片也激动,想要共乐乐。十几年写下来,专栏好像也内化成我生活的一部分,遇到好人好事要说一下,遇到坏人坏事要打一下,虽然我知道很多时候也是自娱自乐或自欺欺人,因为专栏的成效微乎其微。
南都:从青涩的新锐专栏作家成长为如今通行于两岸三地华文世界的学者兼作家,你觉得自己有什么特点或者特质?
毛尖:哦,这个评价我当不起。一定要说的话,我会说我的特点大概是比较通俗,再加上我好歹还有学院的身份,也就是说,我有自己的专业。因为对通俗的追求,我很少掉书袋;又因为在高校里,周围都是高手,像我的师兄罗岗、文尖这些人,都是牛人,所以我写东西不敢瞎扯,不敢跨界乱说。两方面结合吧,我对写专栏这件事有蛮大的敬畏感,不敢在不是自己专业的领域里乱扯;同时又比较自觉追求写得好看点、通俗点,文章写完,一般我会读上两遍,拗口的地方删掉,大概我对虚词的使用有点追求吧。
南都:较早之前,有朋友曾警示你要警惕油滑的倾向,从最初的文章到现在这本《有一只老虎在浴室》,你觉得自己的写作愈发严肃了?
毛尖:严肃和油滑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说越来越严肃,主要是说我写专栏的主题及写专栏的心情。我承认,最早写专栏是好玩,觉得有趣。之前有些文章,的确有人批评有油滑的倾向,对我文章中的一些段子特别看不惯。我承认这些批评很中肯,对我也是一个警醒。不过,我对段子一直情有独钟,好的段子几乎就是生活真理的凝结。如果这是低级趣味,那么我会坚持自己的这点低级趣味。至于说到严肃,从开写第一年到现在,我的心情确实是越来越严肃。因为这些年自己的身份也在变化中,结了婚、当了妈,社会责任感相对而言增强了,对自己看不惯的东西,原来可以闭眼的,现在就会比较疾言厉色,进入专栏时候,声音有时就会比较严厉,张力弱了,有些朋友就会批评我,没有以前放松状态下写的文章好看。我想,这之间是一个平衡吧,我还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
南都:总有人说专栏作家与时代脉搏接得太紧,会太浮躁,静不下来。你自己觉得呢?
毛尖:专栏作家做的就是一线的活。浮躁是贬义的说法,可如果往好里说,专栏作家不怕死,不怕被人骂,也是火线战士啊。一般情况下,我们总是在第一时间发言,不会说别人发完言,我们再总结一下,那当然比较保险,但我们不行,专栏是有新闻性的,我们需要在事情发生的时刻作出评论,一旦说错话,就会被人骂浮躁。这是我为我们这个行业辩解的说法,当然,本质上,我们自己肯定也的的确确有浮躁的时候,这跟个人修养有关,所以,写专栏,确实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触碰的话题,还是禁忌,那如何在能碰的范围内去碰到极限,这个既是技巧,也是修炼。所以我常觉得,我们写专栏的,就是踩点的。有时候说得不对头,就会被口水淹死。
说起来也挺辛酸,我们专栏作家一直在干累死累活的事情,却又常常没有名分。主流上来说,我们不是作家,而读者也觉得我们像打手一样,很像美剧《24小时》里的杰克鲍尔一样,一发生事情,我们马上背着子弹就出发了,有时还打到自己人,或者是打歪掉,还被人骂,你说我们像不像小强?(笑)
南都:“稍微轻浮了点”、“有口水话的倾向”……这样一些声音好像自你写作起就一直都没有停过。
毛尖:前面说了,一个因为我经常使用段子,我其实从不否认我这个追求,而且我也不会停止使用段子,因为段子是民间文化的集锦,也不会因为别人觉得我轻浮就不写了。另外一方面,我也想说,其实口水是一种能力,我反而觉得自己没有口水的能力。我上课累说话快,就是口水能力差。张爱玲厉害的地方,就是她有说废话的能力,这种能力,我们华师大倪文尖老师有专门研究的。我其实没有这种说废话的能力。
俗文化里有很灿烂的东西
南都:你曾把自己形容成“这种出生就迷上电影的可怜人”?
毛尖:这个“可怜”肯定是后来才加上去的。因为以前肯定是幸福的,对于我们70后来说,没有谁会不喜欢电影。因为那时候老百姓生活中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影。那时《大众电影》的发行量是八百万份,人人都是影迷。而且,我们这一代可以说都是通过电影受教育,通过电影和主流价值观进行交往。
而说成为可怜人,是因为现在都是烂片啊。好几年前了,一次和大家吃饭,吃到一半跟他们说我要去看《三枪》,就被大家嘲笑说那个烂片你还去看。可是因为半职业影评人的关系,每年要参加几次评奖,所以什么电影都要看,烂片也要看。你不看就不能说它烂,所以我有时候感觉自己像扫地工一样,什么东西都要去扫一下,这个是身份决定的。其实,每次去看一个事先张扬的烂片,每次我还总隐约地抱希望,万一人家有一些闪光点呢?当然,看过的电影,80%以上是烂片,这不是很可怜吗?
南都:在《有一只老虎在浴室》里你写到,当今世界,低俗就是生产力。相比伍迪艾伦的知识分子气,疲惫的草根当然更需要虽然猥亵但还算健康的笑料。现代社会这种所谓“娱乐至死”或者“低俗”的趋势似乎愈发的明显了,你怎么看待呢?
毛尖:我基本上也承认这个趋势。不过如果死心塌地地承认这个趋势,那影评人这个工作就没法做了,所以我也一直抱希望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吧,或者说,烂片里也有金子吧。另外,关于低俗这个事,我认为低和俗还是要分开来,现在基本上把它们笼统放在一起。很多情况下低其实是不够俗。俗本身是蛮好的,我也挺喜欢俗,但现在电影基本做不到俗。俗文化里面有灿烂的东西,有常识。但现在大家都一股脑儿把低和俗搞在一起,有点分不清了。
南都:会被什么样的电影所吸引?会怎么琢磨怎样的故事?
毛尖:因为自己这些年都在评华语电影,所以如果一部中国电影和一部外国电影同时上映的话,还是会先去看中国电影。至于说到爱好,这几年我都在关心黑帮电影,我们会在黑帮电影上看到那种坏到没有心肠的东西,而在这种无限的黑暗中,也会诞生出黑的崇高性,我喜欢这种“理查三世”式的黑色崇高。像最近看的《消失的女孩》,女主相当黑,我喜欢。我的意思是,在一个正面的崇高性出不来的时代,反面的崇高性也可能是一种激励。我对软弱的心灵一直很讨厌,讨厌那种疲惫的、怯弱的、娘娘腔的东西,所以,我想用“黑色崇高”来反向批评一下当下电影界的娘气。
南都:中国电影的发展态势可否简单谈一谈?
毛尖:当下的中国电影简直是另外一种东西,就像现在弹幕电影出来,电影的语法都没了。粉丝电影的天下,有钱就能拍电影,电影的态势怎么谈?当然,我也不能说不抱希望,至少姜文、贾樟柯都还在拍电影,虽然他们这几年拍的电影我自己也不是特别喜欢,但我觉得他们的元气还在,总还有希望在。但整体来说,真的很悲观,我也一点都不想掩饰自己的这种悲观。
未来非常长的时间内,专栏文字都将会是一个文化的频道南都:这十多年来,专栏文字在报刊上像火焰一样跳动,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泛滥的时代。你是其中的一员,同时也被认为是其中最优秀者之一,你自己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
毛尖:如果从文学样式来说,一个平庸的时代或者说碎片化的时代,就会是一个散文的时代。然后呢,现在也是一个媒体称霸的时代,在未来非常长的时间内,专栏文字都将会是一个文化的重要频道。
所以相对来说,现在做一个专栏作家应该还是蛮幸运的,好像赶上了这个时代。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专栏作家,你又会觉得,这个时代如此平庸,一切都转瞬即逝,甚至看个标题就足够,我也不否认自己有时也会写一些没有一点意思的文章。置身这样的碎片化的、平庸的时代,即使你是一个著名的专栏作家,又有什么意思呢?这里面,你有你的一个幸运感,你也有一个你的失落感,一个巨大的失落感。
南都:现在专栏作家是不是比以前级别要高了?
毛尖:级别高了可能是一方面,因为专栏作家也慢慢地进入了一个主流文化圈,像你们会把奖颁给我,就是一个证明。另外一方面,是专栏作家队伍越来越庞大,写专栏的人越来越多,也有很多主流作家进入了专栏作家的行列。这有点像电影、电视剧的关系。原来电视剧是被人看不起的,我自己以前也是不看电视剧的。但是现在一线的演员进入电视圈了,美国《纸牌屋》不都是一些一线演员在拍吗?我们的孙红雷、陈道明不也在电视剧做得风生水起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位置的重新排序。像美国的艾美奖,现在观众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奥斯卡奖,嘉宾请得比奥斯卡奖的嘉宾还厉害。因此,在这个时代,我们就像搞电视剧的人,慢慢的也被搞电影的人所承认、接受。
南都:如果和其他以散文文体写作的作家对比,专栏作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毛尖:专栏作家就是个勤务兵,是扫地的。把现场打扫乾净之后,散文家可以出来抒情。(笑)我以前从来不敢说自己是作家,但是现在作家的光环下来了,觉得当个作家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小时候,老师让我们写理想,我们如果要写“作家”,老师肯定觉得你疯了!中学时办过一个文学杂志,给很多上海的一线作家写信,我们都是怀着崇高的、甚至手都发抖的心情写的。那个时候作家的头上是有光环的,现在谁都是作家,或者说很多网络上的人说自己是写字的时候,其实都把自己当作家看。这是一个作家泛滥的时代,作家光环消失的时代,所以现在你把我叫做作家我也没有觉得有多大的荣耀。这种生态其实在校园里就很有感受。以前校花都是嫁给作家、诗人的,现在谁嫁给作家诗人啊?都嫁给CEO什么的,作家这个身份现在要接受市场的评价了。
南都:怀念那个时代吗?
毛尖:还是蛮怀念作家身上有光环的时代。我宁愿人们说起专栏作家时,觉得不如作家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人们脸上的表情也都更清贫一点,人和人的关系更纯洁一点。这就像那个时代去看电影一样,我们一分钟都不愿意错过。那时候看电影是一种盛典,外婆、妈妈从单位回来,会换下脏衣服才去电影院,看电影有一种仪式感、朝圣感,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南都:作家阿来说你的写作,代表了文学一个新的样态。和他们那一代相比,若是邀你把散文放到散文期刊上发表,你自己可能都不愿意?
毛尖:确实受众主要已经不在那些刊物上了,但我当然还是愿意去这些主流刊物发表文章,这和我从小的向往有关系。以前有朋友在《收获》发文章,还从县里调到市里。
南都:相较各种小说、杂文、诗歌这些体裁的分野,字数才是你的体裁?
毛尖:对,这跟我写专栏有关系。最早在信报上写,规定是七百五十字,后来在东方早报写,东早书评是五千字,随笔则是一千六百字左右,所以,严格按照字数写文章。有人约稿,我不会问你要我写散文还是写诗歌,总是在第一时间问对方多少字数。还比如,布置学生一点作业,他们也总在第一时间问字数。字数改变了这个时代的节奏。从博客到微博到微信,就是字数的改变。我觉得字数就是时代节奏的显形,或者说,这是时代节奏进入到我们文学写作中来了。
南都:你曾说,自己一直以为将来是要写小说的。现在呢?是否打算换一换写作方式?
毛尖:一直有师友劝我、鼓励我可以写写小说,包括影评圈里,有朋友劝我尝试做编剧。这样的诱惑一直有,我承认自己也受到这种诱惑,但我想自己暂时不会。首先,我现在没有这个时间和体力。写小说是长跑的活,我现在适合短跑。而且,我现在的短跑工作也不是没有意义,通俗地说,当下,专栏写作还是一个传递能量的东西,在当下也有它的一个位置。
南都:可能性还是有?
毛尖:如果可能的话,以后去角逐一下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新人奖(笑)。
南都:你好像很看重文化批评,觉得透过文化批评也能够实现自己的写作梦想?
毛尖:对。不过如果我实现了梦想,你们应该考虑颁我一个华语文学评论家奖。我现在肯定是没有实现,所以你们给我一个散文家奖项。(笑)其实我觉得我的位置一直挺模棱两可,有时候别人叫我作家,有时候叫我学者,我自己也随便人家怎么说,我觉得什么位置都能认可,但最终可能确实是一个批评家的位置。
这个跟我的朋友圈有关系,我的导师王晓明,我的师友罗岗、薛毅、文尖、启立、炼红、晓忠、春林他们都在做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工作,大家觉得有义务在这个时代承担一个中国文化人的责任。尤其在学校里能够感受到,虽然学校里的生态可能是恶化得最慢的,但是能感受到近几年生态的持续恶化。比如以前感觉老师是教育者,现在有时感觉老师像唱堂会一样。落差太大了,就这么十年之间。不过,不管怎样,我觉得自己无论当老师还是写作,我的态度还是比较一致的。相对来说,我还是希望有所为吧。
来源|南方都市报 本网编辑|戴勇 阅读原文
其他媒体报道:
I时代报|毛尖: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 阅读原文
宁波晚报|宁波籍作家毛尖获得年度散文家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