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上海“悦悦文化”邀请各地著名学者和作家分享自己的阅读经验和推荐书目,为读者奉上一份“抗疫书单”。
孙甘露(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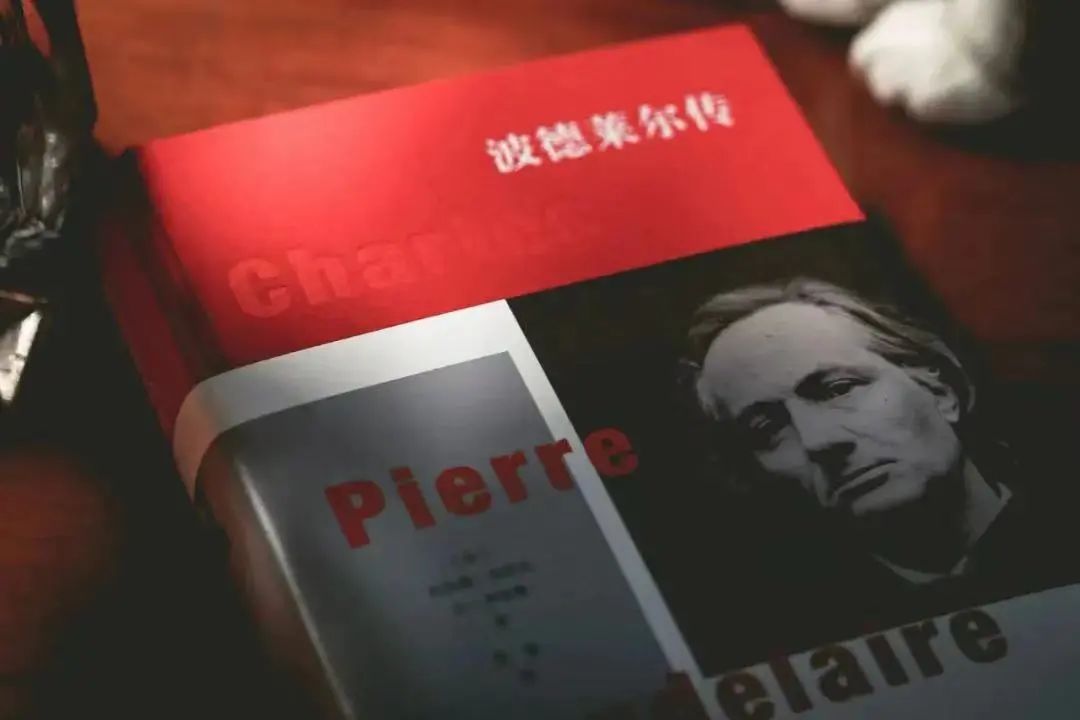
祝悦悦图书的朋友们,愉快地阅读,通过“悦读”飞跃禁锢。我推荐克洛德·皮舒瓦与让·齐格勒合著的《波德莱尔传》(董强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出版)。
王为松(上海社科联党组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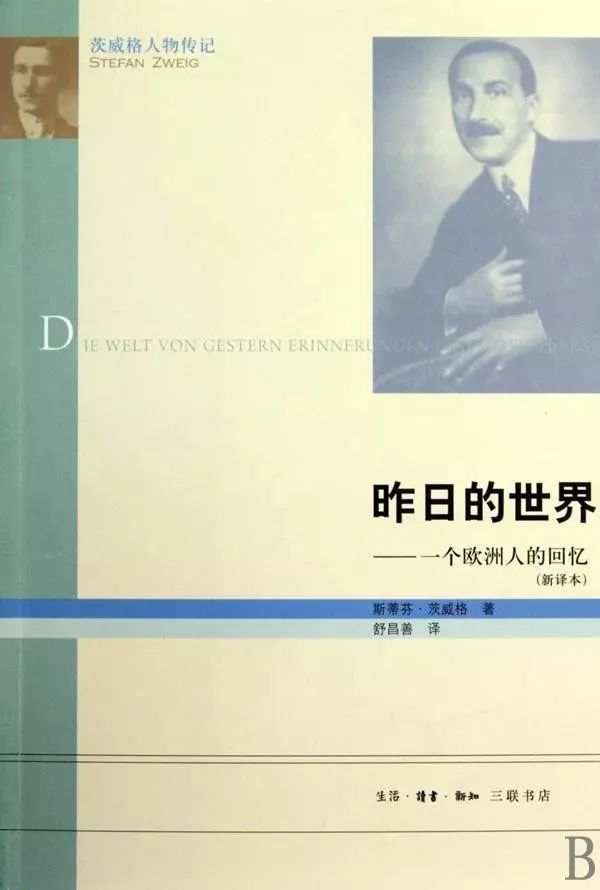
我推荐一本值得再看的老书: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舒昌善译,三联书店出版。
一个写《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一个女人的二十四小时》的奥地利作家,常常在他的世界主义的梦幻里想象这样的场景:让所有人没有区别地生活在一起。虽然他后来在巴西看到了心中的未来之国,但作为一个把欧洲文化视作自己性命的作家、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他不巧碰到了一个让他的精神世界彻底崩塌的时代,无休止的火山般的激烈震荡,摧毁了他的生活家园与精神家园。他不再追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因为,他觉得我们没有义务因为世界变得荒谬,我们也要随之变得荒谬。这是他对当年欧洲的失望,也让我们在一个相对静止的时间里,去更多地了解历史,再来反观自身、思考未来。
如果读者还想有更多了解,可以去看2016年玛利亚·施拉德导演的茨威格的传记电影《黎明之前》。
张广智 ( 复旦大学教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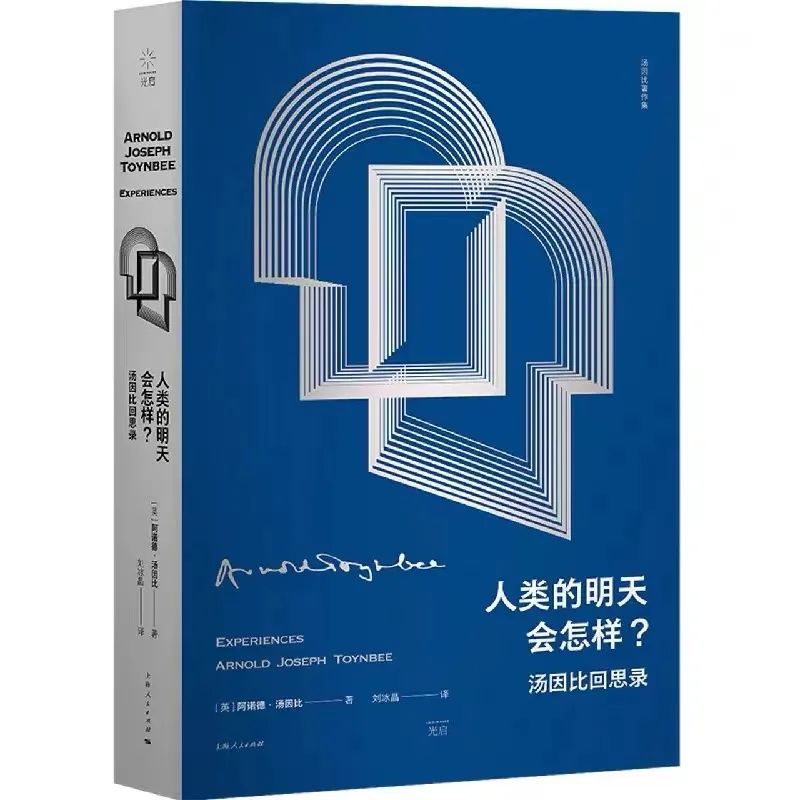
当下,疫情骤紧,新冠肆虐,浦江两岸笼罩在一片雾霾之中,面对这严峻的时刻,唯有我们万众一心,风雨同舟,才能打好这一仗!
明天,浦西地区实施封控,无论是冲锋在前的,还是宅家的,都是跟病毒战斗,共克时艰。就大多数市民而言,都要闷在家里,那逼仄的环境,令人郁闷,但这并不能束缚人们思想自由的空间,更不能桎梏有志者的心灵。宅家是防控病毒的仙丹,读书是缓解焦虑的良药,不是吗?正如毛姆的名言所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静心阅读,阅读的春天,将会永远在每个读者心中,绽放出各自绚丽的光彩!
遵“悦悦图书”之嘱,我向各位读者朋友推荐一本书:《人类的明天会怎样?——汤因比回思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版)。我为这位现代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自传的荐言是:汤因比逝世已近半个世纪了,但他似乎还活着,活在他的著作中,活在这位“智者”的“警世良言”中,活在世间每个个体生命的心田中,清新、鲜活而又透彻,其言醍醐灌顶,其声振聋发聩,倘问汤因比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在我看来就两个字:“希望”。希望,希望啊!我们的追求,世人的理想,为前行者带来了无穷的力量。悠悠千载,前路漫漫,行囊中始终只装着一份希望。让我们同心抗疫,迈着雄健的步伐,带着希望一起向未来!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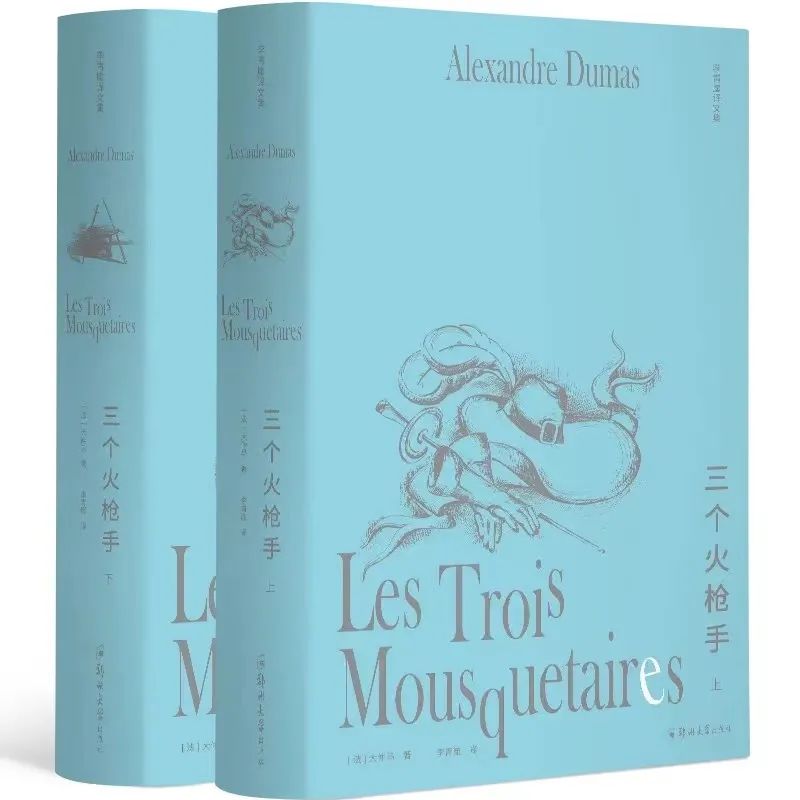
大疫中读书,至少对我来讲,是极为难得的体验。正好收到一套《李青崖译文集》(郑州大学出版社),共七种,据说还有。李青崖这个名字,我这代人知道的应不少。他老人家是翻译法国文学的大家,以译莫泊桑、福楼拜、大仲马、左拉等著称。他1969年就去世了,那时我正在读他译的莫泊桑,读得入迷。现在想想,这真是一种可怕的体验,你在读一位译者译的书,而不知道他正在走向死亡。所以,足不出户时,再重温一下年轻时爱读的书吧。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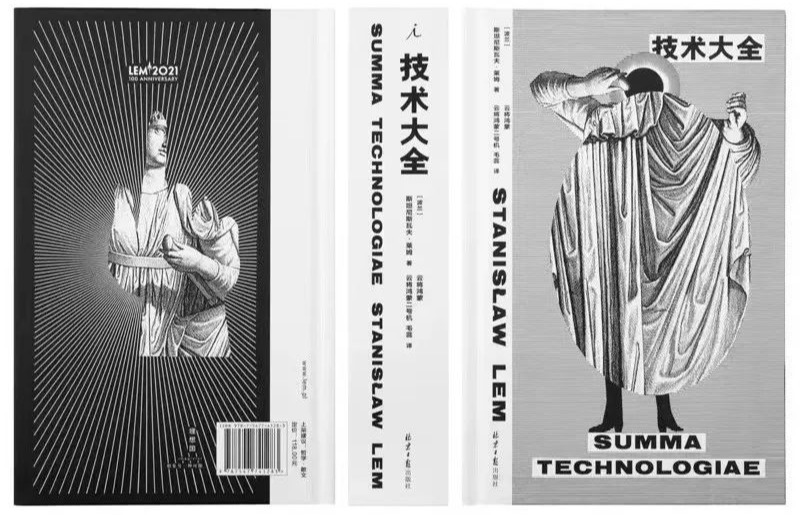
封闭期间安心读书,原是很好的想法,不过真要做到也不容易,必须努力不让各种纷至沓来的无用信息干扰自己。
荐书:《技术大全》,(波兰)莱姆著,云将鸿蒙等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1月第1版。科幻小说。
荐电影:《霍乱时期的爱情》(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2007)。根据马尔克斯同名小说改编,略能应景。
傅刚(北京大学教授)
上海受疫情影响,全城进入静默状态,东方明珠,竟蒙尘埃,为上海忧心,为上海人忧心!诚祝上海全体人民,包括我们悦悦图书的读者们能够战胜疫情,克服时艰!
上海是伟大的城市,上海人也是伟大的人民,你们之前在抗疫时为全国人民作出过示范,相信此次亦能再为示范!我于年初亦曾在上海隔离14天,至年底春节时又在北京被隔离14天,我深知隔离困居于斗方之中的煎熬,但既然遇上了,就要面对,我的破解苦闷之方是读些书,听些音乐,每天做一些有乐趣的运动,保持乐观的情绪,以此获得心下平衡和安定。急躁、焦躁、忧虑有时难免,但要清楚明白这是有害的情绪,一定要想办法阹除掉。何以阹除,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能够使心安静,不迷茫,都可以尝试。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疫情也终是过眼云烟,上海终会重放明珠的光芒!读何种书、听何种音乐,皆随个人喜爱。我喜欢听的是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以及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它会让人的灵魂安静下来。当然,听听自己喜欢的流行歌曲也能有安定自己的效果,在保持乐观的前提下,选择什么样的书、音乐、电影,都据个人兴趣而定。最后祝各位身心健康!早日战胜疫情,我们与你们同在!
李天纲(复旦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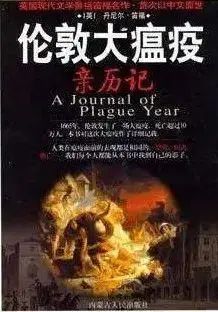
浦东、浦西,相继封闭,市民难免有些恐慌。然而我们要说:疫情当前,最不应该慌张的就是上海人。城市里有句老话说得好:上海人什么没见过?自1843年11月“开埠”以来,上海经受过的全球性瘟疫不下数十次,很多就是从上海登陆的。大城市有福利,当然也有风险,市民们都必须从容应对,且在应对中完善自己的城市制度,让它变得更强大。值得担忧的只是,这个城市里一百多年的自治制度和传统不断流失,令市民的自组织(autonomy)精神衰退。如果这次全民抗疫能够推动此种精神的复兴,那我们在疫后能够收复的就不止是一座健康的城市。
推荐一本书:笛福的《伦敦大瘟疫亲历记》(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本书是笛福作品中读者较少的作品,作者以纪事的笔调描写了1665年的英国和欧洲的大鼠疫。瘟疫在伦敦造成10万人死亡,全市人口损失十分之一。这场介于中世纪和现代社会的瘟疫,推进了近代城市制度和现代卫生体系的建立,现代文明就此更新,而人类则进入了持续繁荣的新时期。
傅杰(浙江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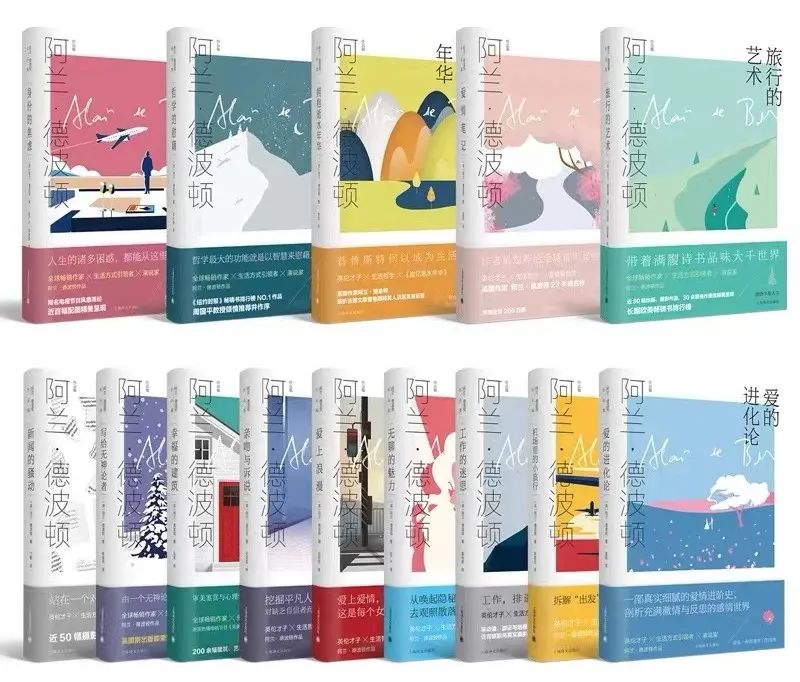
从无奈地来到无奈地去,我们凡人一生中总会遭遇无数个大大小小无奈的时刻,只要还没有沦落到饥寒交迫精神错乱的境地,读书人最无奈的应对方式也就是读书了。悦悦图书征求供读者在因疫情被迫赋闲时消遣的书单,我推荐选读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作品集(包括这位英国作家的《哲学的慰藉》《身份的焦虑》《旅行的艺术》《幸福的建筑》《新闻的骚动》《工作的迷思》《无聊的魅力》《爱的进化论》《拥抱逝水年华》《写给无神论者》《机场里的小旅行》以及《爱情笔记》《爱上浪漫》《亲吻与诉说》三部小说,另如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等还出过他的《艺术的慰藉》等)。读者既容易在他涉及广泛的多部作品中找见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读来也应不无所思不无所乐不无所获。
陈正宏(复旦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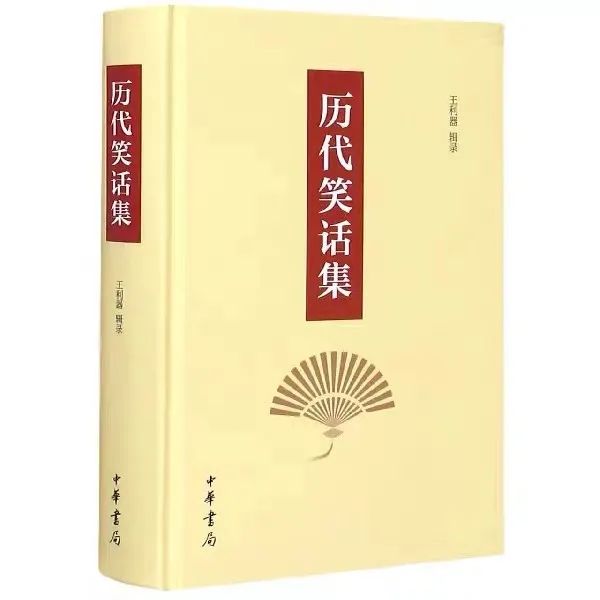
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故疫情之下,最好的应对,一是居家全身心投入地办公或学习,那样或可以省下不止一顿的饭和菜;二是每天至少让自己大笑一回,并即时忘却眼前的忧愁和恐惧。前者稍易,后者实难,我因此推荐各位看一书——王利器先生辑《历代笑话集》(中华书局,2020年版)。
王宏图(复旦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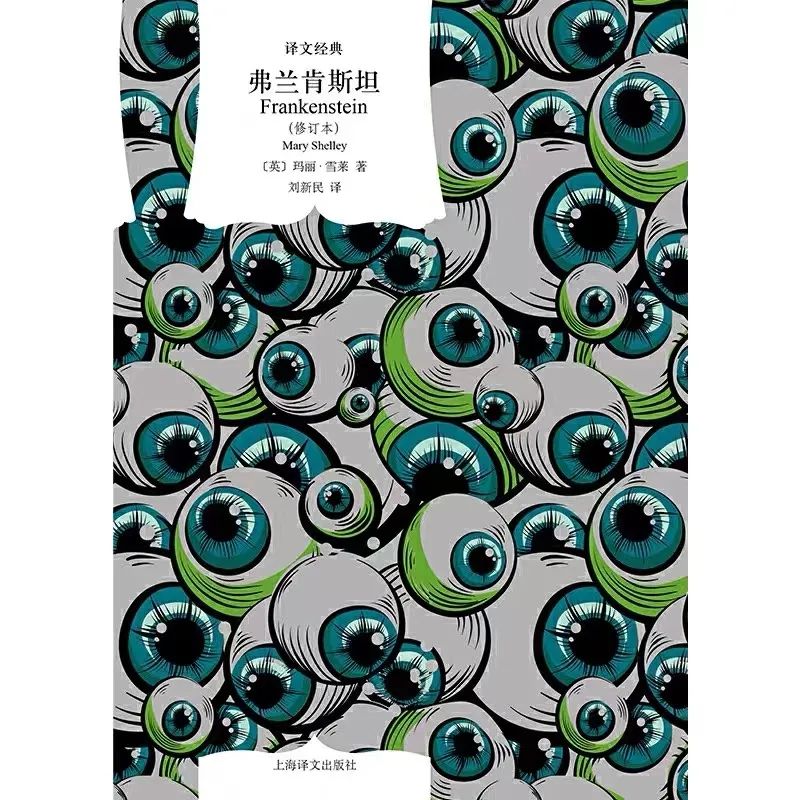
疫情滔滔,禁足室内,郁闷之情盘绕于心。物理空间虽狭逼,但窒息不了对远方的向往;净心默祷,期待重新翱翔于蓝天碧海之间的那一刻。特殊时期推荐英国诗人雪莱的夫人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这是一部神奇之作,将哥特式的惊悚故事和科幻奇想融于一体,而且触及到人性深处诸多幽秘角落。静心之际,可在其中找到最时髦的元宇宙的诸多元素。
汪春泓(香港岭南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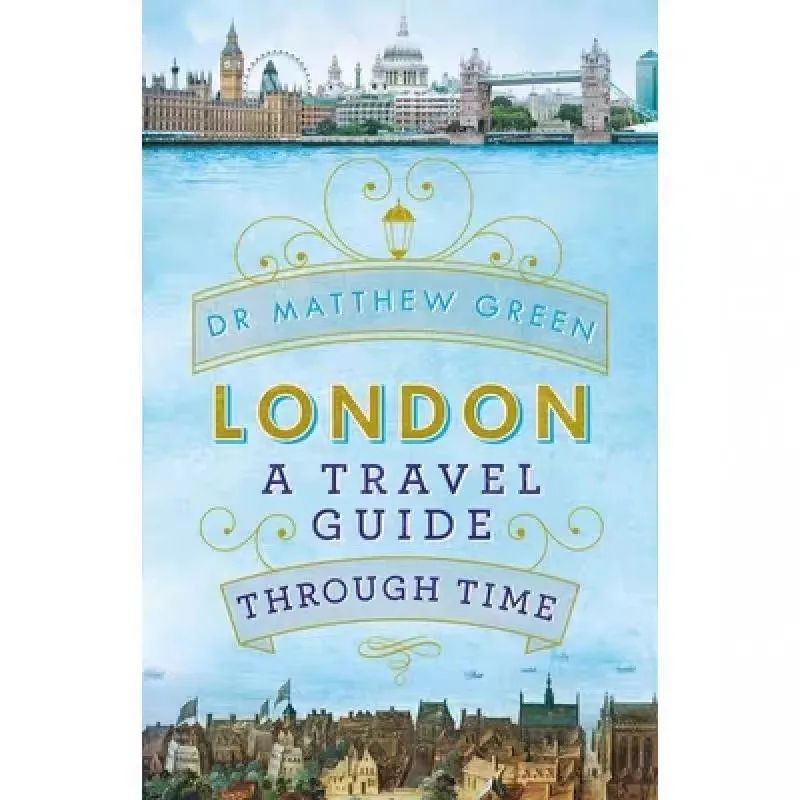
君子居易以俟命。在这个纷扰的世界里,我们读书人只能以此自勉,管理好自己,以平常心做日常的功课。由于不能出游,所以暂且卧游,我推荐一本书:DR MATTHEW GREEN 所撰的LONDON:A TRAVEL GUIDE THROUGH TIME
严锋(复旦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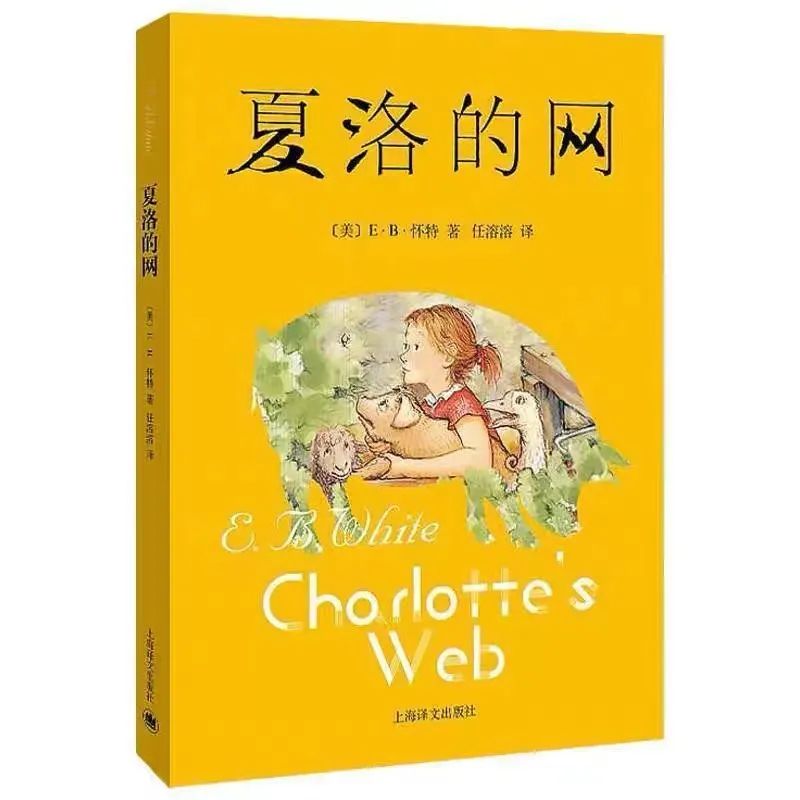
越是在封闭、争吵、焦躁的时候,越是需要暂停一下,从消极的循环中跳出来,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天空,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心情。怀特《夏洛的网》 在我有生之年里,大概过两三年就要把这本书找得来看一遍,好像病人要定期吃药那样。遇到一些额外不顺心的事情,就还会额外不定期地服用。服用之后便觉天高日丽,神完气足,心清肺明,好似用光了的蓄电池充足了电,又可以投入到人世间的损耗中去。
郜元宝(复旦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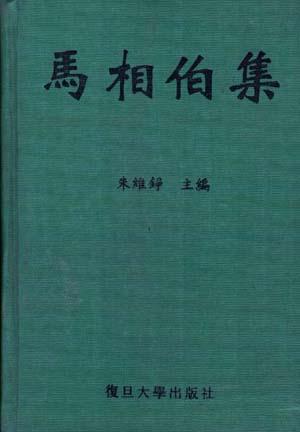
深陷疫区,甚为惶恐与不便。但尚能读书度日,已属万幸。特荐读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这不仅是复旦学子(乃至举国学子)必读之书,凡我国人而能识文断字者,亦不妨一读。至少可以籍此了解“百岁爱国老人”如何遭逢与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该老人究竟如何“爱国”,或可与今日“爱国”之各种定义、各种言行作一参照,并有助于观察今日之所谓“变局”也。
毛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特别羡慕没有看过《权力的游戏》(2011-2017)的人,就好像你还不曾动用过生命中最丰饶的奖赏。没有比漫长的封控期更适合用来看七季(对,最后第八季不要看)《权游》了。一口气看完它们,如此,再惊悚的人事找上你,你都可以用二丫的语气说:NOT TODAY。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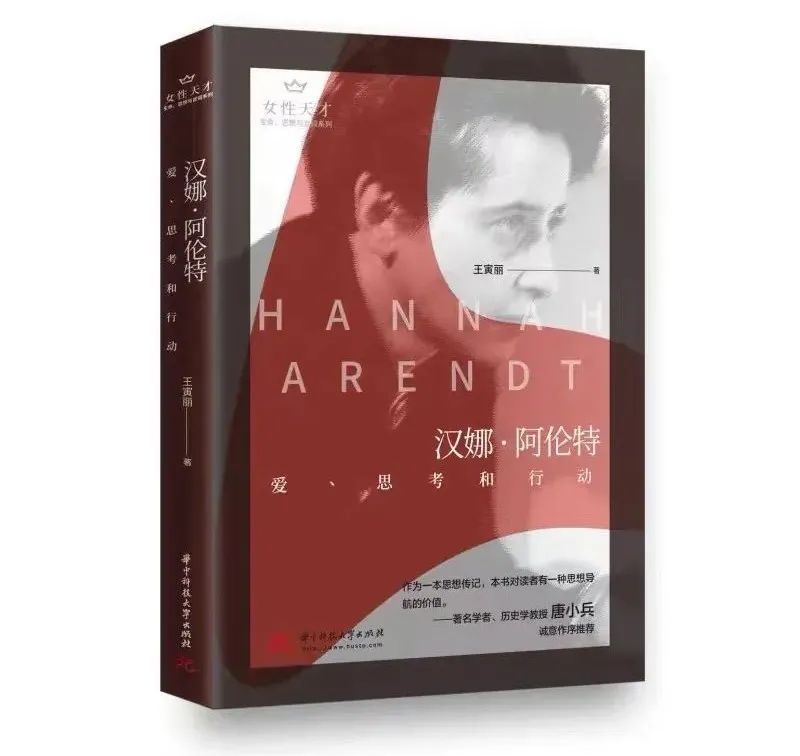
2021年学界前辈何兆武、章开沅、余英时、李泽厚先生等相继逝世,感觉是一个天才淡出巨星凋零的年份,我这些年持续思考的问题是现代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在当下中国何以得以延续、深化、拓展而赓续不绝,而人文主义传统寄托于像前述这样的知识贵族和学术大家,他们以自身的学术、人格和选择彰显了即使在一个人文精神式微的时代,坚持文化、智慧与学术的尊严仍旧有其不可剥夺的价值。围绕这个主题,我今年重点阅读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三本书,包括日本思想史大家丸山真男的论文集《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谢正光的文集《清初的遗民与贰臣》和杨潇的非虚构作品《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丸山真男的作品彰显了日本思想史复杂的张力和内在脉络,也展示了近代日本知识人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选择,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谢正光先生的作品则展现了清初遗民与贰臣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勾连,显示了人性与政治彼此交错的历史世界与精神图谱;杨潇的这本书通过公路行走的方式将历史写作与旅行写作做了极好的内在结合,呈现了面对个体和人类困境的自我如何向历史与自然汲取强韧的心力来摆脱结构性状态的自觉。三本书构成了一个互相参照极为有趣的知识世界与精神地图。
我最近在阅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一套女性天才:生命、思想与言词系列,都是国内最优秀的一批传记作者(都是女性学者)为阿伦特、西蒙娜薇依、伍尔夫、波伏娃、桑塔格、阿特伍德、杜拉斯、沃克等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思想家和作家撰写的本土传记。这套书思想、学术与文化的含量都很高,我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王寅丽教授的《阿伦特:爱、思考和行动》撰写了序言,也读完了贵州大学哲学系林早老师写的《西蒙娜薇依:为万般沉默放行》,极为触动,作者错落有致地展现了薇依的生命历程、政治实践与精神世界,后者宁可放弃出身贵族的优越生活,而将自己放置在最艰苦的人群和境地去感同身受地承受世界的苦难的选择,并为陷溺在困境中的人类探寻精神的出路,这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才是真正的左翼知识人和贵族精神,作者可谓薇依的隔代知音。这套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书系虽然零星地受到关注,却并未引起知识界、书评界热议或被出版界高度关注,这让人深感遗憾,我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向读者推荐。
方笑一(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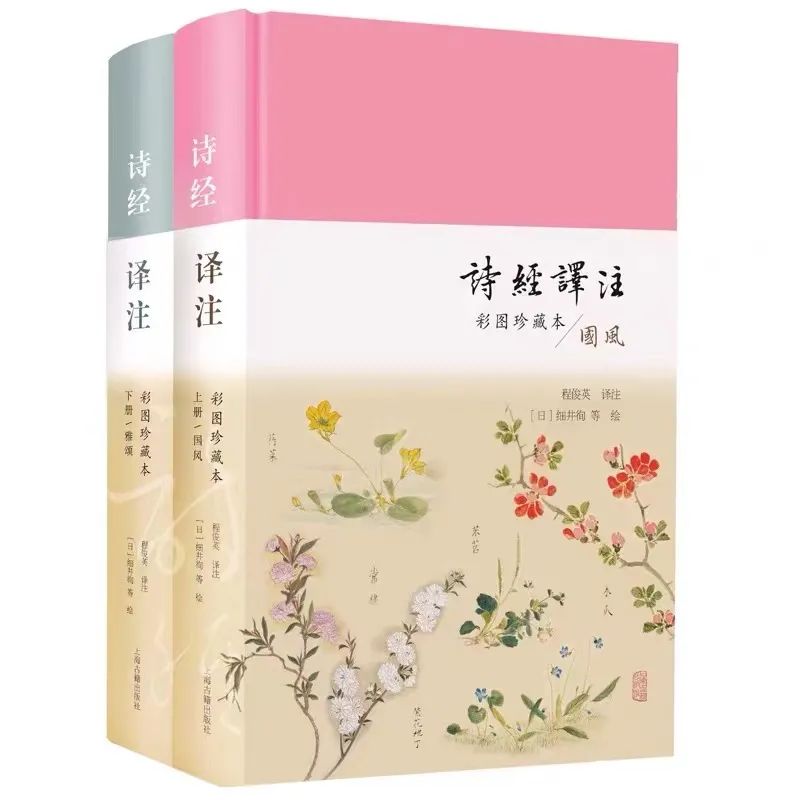
悦悦图书的读者朋友们:疫情让上海的节奏和你的节奏都慢下来,平日里,“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此刻,身心都交付给你自己安排。读书,不失为一种悦己之道。推荐几本书。
一、《诗经译注》,程俊英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最亲切的古代经典,告诉你2500多年前的中国人如何生活,如何抒情,如何思索。
二、《重游缅湖》,(美)E·B·怀特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精灵鼠小弟》的作者的散文集,自然随性、细致入微的描写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它正可以让你忘掉对“意义”的执念。
三、《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英)罗伯特·瑟维斯,译林出版社2021年。历史转折关头总是惊心动魄,只有历史学家能让我们身临其境。
再推荐几部电影。《安妮·霍尔》,导演:伍迪·艾伦,美国1977年。《阿德尔曼夫妇》,导演:尼古拉斯·贝多斯,法国2017年。《将来的事》,导演:米娅·汉森-洛夫,法国2016年。看起来是男女相处的故事,其实包含了人的所有。
骆玉明(复旦大学教授)
说到读书,如果我介绍大家一两本书的话,我就随口说吧,有一本新校注的《陶庵梦忆》,张岱的。
我们经常说张岱是晚明小品的作家,这样说文学史上也习惯了,也没什么不对,但其实他主要生活在清代初年,他的寿命也很长,活到挺晚的了。他现在流传下来的那些最著名的作品,其实都是在清代写的。按照中国传统习惯,他在清代没有做官,就所谓入清不仕,那么他就被当作是明代人,这是中国古代正史记载人物的一种惯例,这种惯例也成为大家论述一个人物时候的一种习惯,实际上他那些回忆他以往的生活的作品都是在清代写的。
《陶庵梦忆》大家很熟悉,出过很多很多版本,我说的这个版本是栾保群先生校注的,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出版时间不长。
那么我为什么要专门介绍这本书呢?这本书它用的版本比以前的《陶庵梦忆》的版本要好一些,校注的工作也做得相对比较仔细。有的朋友可能读过《陶庵梦忆》,或者在各种选本里面读过《陶庵梦忆》当中的文章,我想,有这么一个新校注本的话,它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阅读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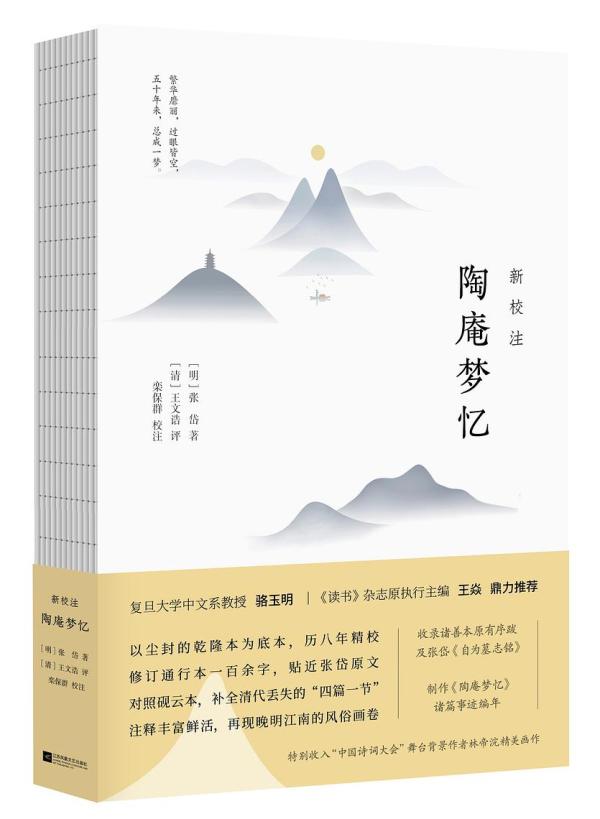
栾先生的校注也做得比较仔细,比较专业,我为什么介绍这本书呢?这本书首先文字非常漂亮,特别当我们读古书的时候,我们对那种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的人会油然地发生一种敬佩。
前不久我在讲韩愈的文章。韩愈这个人大家对他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说得高的,像苏东坡说的“文起八代之衰,一代文宗”,但是也有人不喜欢他,比如周作人就特别不喜欢他。但是我想有一点你不得不肯定,就是韩愈在锻造语汇和语言表达的力量感上,差不多可以说无与伦比,很少有人及得上,因为他是一个对语言非常敏感,对语言的表现力特别有追求,而且效果特别强烈的这样一个人物。我们读韩愈的《进学解》,从头读下来你会发现里面全是成语。为什么全是成语呢?因为他说过的那些话都特别的新鲜,特别的有概括力和表现力,特别的引人注目,所以大量的文字后来都成了成语了。
一个民族的语言是怎么样发展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由那些特别具有创造力的作家不断通过发掘,通过他们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来丰富这种语言,来增加语言的活力。说到这个地方,尽管我刚刚说到周作人不喜欢韩愈,但他特别喜欢晚明小品,像张岱这些人,在语言的这种表现力上来说,可以说韩愈和张岱有共同的地方,就是丰富了中国的语言,他们为中国的语言不断地注入活力。
《陶庵梦忆》的文章都比较短,文字非常的漂亮,适合于以一种不太紧张的、比较轻松的态度去品赏它。这种文章是好文章。
好文章不能简单地说读。就像我们吃到特别好的菜,我们不是说在吃一道菜,我们是在品味一道菜,因为这道菜太好了,我们是在品味一道菜;就像我们喝特别好的茶,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在喝茶,我们在品茶。文章也是这样。特别好的文章,我们不要用最简单的话说我们在读一篇文章,说我们在品味一篇文章,这样更恰当一些,更好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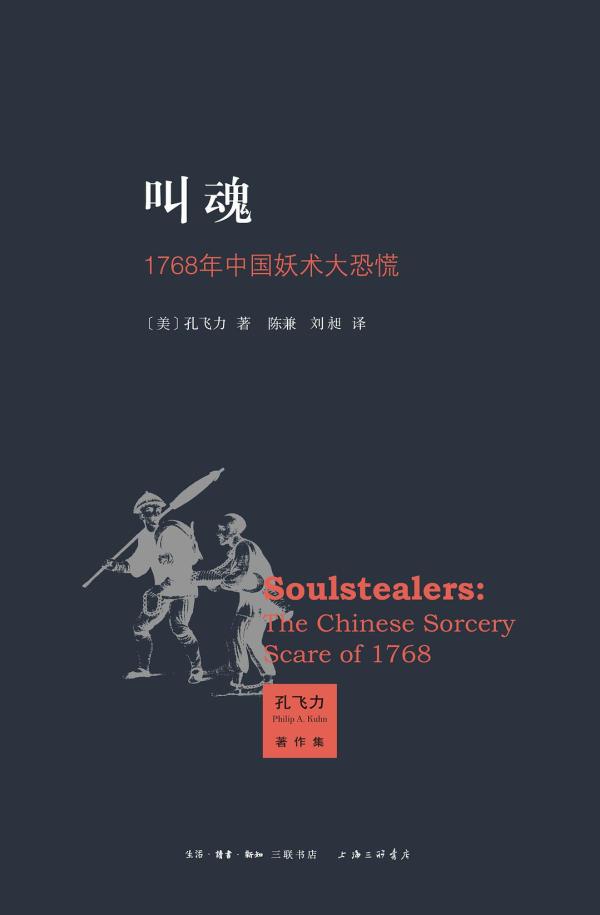
还有一本书是一位美国学者写的,那位学者的中文名字叫孔飞力,他是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的继承人,那本书的名字叫《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本书现在说来也是不新不旧,10年以前三联书店出版的,相比较起来,这本书要严肃一点,学术化程度也要高一点,但是它也是好读的。
中国国内现在还是有那样的一种传统习惯:学术性的著作都是不太通俗化地,通俗化的读物常常学术性不高。当然,这两年已经有所改变了。在国外的出版界里面经常可以看到那种可读性很强、学术性也很强的著作,这类著作对普通读者来说是特别有好处的。
阅读原文
来源丨澎湃新闻
编辑丨赵一航
编审丨郭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