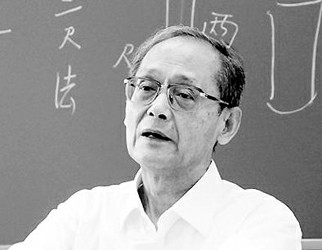

裘锡圭 袁恩桢


章培恒 《王国维全集》
本报记者 田晓玲
黑格尔有过这样一句名言:“一个民族,只有有了那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仰望天空,可以把一个民族的思维带到特殊的高度。一批仰望天空的人同时脚踏实地,使得这个民族的思维具有了坚实的根基。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城市思维高度的集中体现。
2010年,上海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进入第24个年头。1986年,上海首次开展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1995年又率先在全国开展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评选成果评奖活动。
24年来,上海的人文社科成就榜单上,写着张仲礼、蒋学模、刘放桐、王元化、蔡尚思、王养冲、张薰华、王运熙、徐中玉、钱谷融、雍文远、贾植芳等一批学术大家的名字,陈列着《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邓小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中国历史地图集》、《辞海》、《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金文大字典》、《中国文化通志》、《上海通史》、《西方美学通史》、《文学沉思录》、《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移民史》等累累硕果。
所有这些成就,标示着“上海的高度”,代表着“上海的深度”。
在它们的背后,包含着上海学人以天下为己任、以学术为志业的不懈追求。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从中读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思维能力与精神状态。
时代变迁 推动理论不断创新
上海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从来都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生命,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
新中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把中国奇迹铭写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中国发展研究的话语权,理应掌握在中国学者自己手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关事务学院教授林尚立的话,代表着上海学人的普遍心声:“中国的发展需要中国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当今的条件下,需要很好地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
于是,我们看到,“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场景”、“民生论”……一个又一个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学术成果,勾勒出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索。
责任感和使命感,是驱动他们深入研究的动力所在。长期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林尚立说:“我关注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在中国的政治建设和发展中,国家建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无疑是核心的问题。”他的研究,从中国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去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使党建研究和国家建设研究得以有机勾连,以此来展现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可能。
中国的发展,民生为大。对此,长期研究民生问题的社会学家、上海大学教授邓伟志深有感触:“四年前我研究社会矛盾,那时我就发现,要化解社会矛盾,必须抓民生。”和其他领域一样,民生的内涵随社会的变迁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要求社会科学研究为社会大众指明方向。经过多年研究,邓伟志发现,民生不再仅仅是传统的衣食住行,还包括安全问题、环保问题。“有句老话叫‘民以食为天’,实际上还要加一句:‘民以安为地’。在一定程度上,安全比吃饭更重要。当前,我们更应该强调安。”
对于中国社会的变化,上海的学者们一直保持着高度敏感。如何从社会变迁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是学者们的重要担当。早年师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上海大学教授李友梅,对推动社会结构重组的多样性力量长期给予了跟踪研究。同其他许多研究者一样,李友梅深刻感受到,我们现在确实面临着风险社会的挑战。“从全球经济危机到全球大气变化,没有人能够规避风险的纠缠。风险社会作为对中国社会结构重组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力量,在开始形成。”于是,“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中国社会重构的一种新路径”,成了她在“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所做思考的重要成果。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和推动着实践的发展。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任何一种新运动的兴起,任何一个新制度的诞生,任何一项新事业的推进,都离不开理论创新。
19世纪中叶问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理论创新,时至今日,尤其在经历全球金融风暴之后,她对现实的解释力依然那么强大。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始终追求。
一个被人们所反复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资本论》成为当下西方世界人们热烈追捧的经典,人们希望从这部传世经典中寻找到理解和认识当今世界的锁钥。而在东方的中国,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远朋编写的《通俗< 资本论>》一书,更是因其通俗化和大众化的精当解读,赢得了大批读者的喜爱。洪远朋教授长期以来沉浸于《资本论》的研究,《通俗< 资本论>》一书,既不完全拘泥于原著章节,又能完整准确地反映《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和核心思想,深入浅出,同时也联系到当前的社会发展实际。《通俗< 资本论>》成为艰深的理论读物经由学者之手赢得大众的典型案例。
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性研究,是衡量人文社会科学水准的基本标尺。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性研究中,上海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做出了诸多开创性的贡献。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的“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一文,通过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三次翻转的阐释,揭示出形而上学这一哲学核心的本质所在,归纳出其演化的内在规律。而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童世骏的论文“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则将美国哲学家提出的“重叠共识”这一哲学概念同政治文化和实践联系在一起。“西方哲学用了‘重叠共识’这个词,鲜明地提出了如何在多元文化、多元思想的背景下,来维护社会稳定、达成社会共识。”童世骏不仅关注到了这一重要命题,还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理论工作给我们的启发很大,很可以在中国的语境当中也做出相应的思考。”
在中国的语境当中做出思考,才能捕捉到中国发展的真正问题。
中国经济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如今已经难以为继,已经成为共识。如何在这一共识之上进一步找寻到突破瓶颈之路,是上海的青年经济学人、复旦大学教授陆铭的关注所在。他的论文“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特别依赖于省和省之间的市场分割,来保护自己的地方经济,来追求本地的经济增长,结果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丧失了一种规模经济效应。”在陆铭看来,打破这种地区分割,才能为未来5到10年的中国发展寻找到新路。
潜心研究 传承积累中华文化
创新,是学术发展的不竭动力。对人文社会学科研究而言,创新意味着提出新观点、发现新史料、找到新方法。创新绝不是蹈空之想、无根之念;任何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学术研究,背后内含着多少学人潜心研究、文化传承的艰辛与坚持,正是动辄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专心研读,才使学术薪火绵延不绝。
体大博深的王国维学术思想,是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宝藏,不仅涉及文史哲、艺术、教育等诸多领域,同时涉及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等众多20世纪的新兴学科,影响遍及当今。为了填补王国维学术研究领域“没有一部名副其实的全集”这一空白,在王元化、傅璇琮、李学勤、裘锡圭、吴泽、戴家祥等学术前辈的指导下,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经过30年的资料搜集,历时14年的精心整理,终于完成了这部煌煌20卷、840万字的巨作。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先生本人倡导的专注的最高学术境界,在《王国维全集》编撰者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早在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勇在北京做博士后研究时,选择了“庄子学史”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10年后的2008年6月,方勇完成的《庄子学史》才告竣完工。回忆起这个10年,方勇坦言:“这10年当中,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且付出了那么多的艰辛。”为什么愿意付出努力做这样的课题研究?方勇的回答很简洁:“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做出贡献。”在方勇眼里,庄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我想通过对几千年庄子学史的研究,把庄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全方位梳理出来。10年时间很辛苦,也很值得。”
10年辛苦也值得,这种价值取向,是难以用世俗的标准来丈量的。
《中国家谱总目》历时9年积累得以出版,其中的甘苦冷暖,上海图书馆研究员王鹤鸣和他的研究团队,可谓心知肚明。
如所周知,家谱是中国的特殊文献,记载着具有同一血缘的宗族事迹,成为各宗族寻根问祖的一手资料。在《中国家谱总目》之前,业已出版的家谱目录数量较少且多有局限,或为一馆之目,或为一地之目,基础相当薄弱。
上海图书馆接下《中国家谱总目》这一项目后,在前后9年时间里,研究团队寻遍海内外近600家主要藏谱机构及数以千计的个人收藏者,几乎涵盖了海内外收藏中国家谱的主要机构。最终完成的《中国家谱总目》,收录了中国家谱共计52401种,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著录内容丰富,为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利用开发中国家谱资源,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也很好地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网络化对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要求。
无论是团队合作的集体项目,还是独自完成的个人研究,没有皓首穷经、孜孜矻矻坐冷板凳的治学态度,都是难以想象的。
同《中国家谱总目》的编撰一样,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刘钊,对于自己耗时5年编写的《新甲骨文编》也有相似的感触:“以往一直缺乏一本比较全面的甲骨文字典,早的《甲骨文编》写成于六七十年之前。为什么一直没有?就是因为这项工作非常繁难,而且吃力不讨好,有替人做嫁之嫌。出于对整个学术界负责任的考虑,总是需要有人做这项工作的。”如今,《新甲骨文编》出版后,成为甲骨文、商代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
当今中国的经济腾飞与和平崛起,已为世人瞩目,同时,人们更期待中国为大国崛起做好文化准备。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之所以能成为唯一延续至今而没有断层的文明,端赖文化的代代积累和传承。
文化的传承,离不开一代代学人以学术为志业的无私奉献和专业努力。他们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即使是一些非常基础的学术工作,同样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敦煌遗书出土百年,吸引了众多中外学人对其倾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剑英毅然选择了其中研究难度甚高且乏人问津的因明文献作为其研究方向。因明文献的写卷大多以草书写就,且年代久远,卷帙朽蚀,释读不易。同时,这些文本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研究者需要通晓因明学、唯识学及古印度哲学等,理论难度甚高。7年辛苦,沈剑英只希望能“为后人的研究开启方便之门”。
中华文明并非独立于世界其他文明之外,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学习其他文明的先进之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
中国俄语年出版的《汉俄大辞典》,就为中外文明与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这部辞典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汉俄双语工具书,共收录9000多个汉语单字、12万余词条、总字数近1000万。对此,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专门致信给编写人员和出版社表示祝贺,认为辞典“为深化俄中人文领域的合作做出了切实贡献”。
经世致用 服务科学发展
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的责任。谈起针对现实问题所做的研究,上海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总能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不论是总体发展战略,还是具体政策实施,上海的学者都做出了自己的独到贡献。
当“科学发展”成为中国的时代发展主题时,上海的学者明确认清了在全社会培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巨大责任。
2006年底,“又好又快发展”成了我国发展的新战略。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看似一字次序之差,表明了发展理念的根本调整,即把质量摆在首位,发展速度要受发展质量制约。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王国平及时关注到了这一细微而又重大的变化,他的论文“‘又好又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分析认为,“又好又快发展”实际上展示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新道路,即经济持续增长、结构趋于优化、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挑战机遇将伴随现代化进程。
这一深入解读,为大家更清晰地理解科学发展新战略提供了学理支撑。
科学发展观不仅体现在发展方针和总体方略上,也体现在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众多没有标准答案的新问题新矛盾,亟待各研究领域的专家为此提供智力支持。
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一直就是困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大问题。对于处在特殊发展阶段的特大城市上海而言,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显得更为紧迫。
“户籍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思考”,是复旦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彭希哲多年思考的结果。在彭希哲看来,户籍本身的改革并不复杂,但由于户籍改革涉及教育、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等社会管理体制的多方面变革,从而成为一个综合性难题。从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思路来寻求解决之道,正是彭希哲基于上述立场提出来的“药方”。
过去30年,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推动了经济发展,被认为是“中国模式”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竞争也造成了重复建设、资源浪费、规模不经济等问题。究竟怎样的地方政府竞争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是最有帮助的?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汪伟全经过研究发现:“竞争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政府会表现出积极竞争,有时候表现为消极竞争?制度的完善与否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往往是社会变革、制度创新的理论先导。社会转型越急剧,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越突出。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学金关于大都市人口和创新关系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潘英丽关于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高帆关于中国各省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研究等等,都是上海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充分发挥政府决策思想库、智囊团作用的典范,对推动国家和上海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社会大变革,催生了诸多更具现实性的新问题、新产业、新技术,人们对这些新事物还比较陌生,认识还不够全面,更加需要理论工作者的指点。如今,上海大学教授史东辉对大型民用飞机产业所做的研究,其中的许多观点和建议已经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大型飞机重大专项论证组所采纳,也推动了大飞机项目落户上海。
和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一样,社会科学同样需要潜心研究,做辛苦但值得的事情。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权衡回忆起自己写作《收入流动与自由发展》一书的情景时颇有感触:“这本书大部分是我在印度做访问学者期间完成的。能够获奖,我的一个体会就是,从事学术研究,有一份付出,才有一份回报。我在印度做了将近9个月的调研,当时天气非常炎热,而且经常断电,电脑写作时经常断电,写作因此被打断。我就坐在那里等,电来了再重新开始。”
炎热的夏天,孤寂的学术研究氛围,让权衡深深意识到,学术研究需要苦行僧的精神,需要枯灯静坐的定力。
热爱与奉献,把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术研究引向更深与更远的境界。
代代相传 学术至上精神一脉相承
2004年开始设立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是上海每届社科评奖中分量最重的一个奖项。6年来,这份名单上,已经写上了张仲礼、王元化、蒋学模等12位上海学术大家的名字。
学术贡献奖重点奖励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原创性、基础性和广泛影响的学术观点提出者。
与这一标准相比,一种无形的标准似乎更为重要,那就是:获奖者必须得到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普遍公认。
今年,又有三位老先生的名字,将写入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的名册上,他们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章培恒,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袁恩桢。
数位推荐人在自己的推荐语中,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实至名归”、“当之无愧”这样分量极重的字眼。
这三位著名学者,不仅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而且对学术界乃至全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裘锡圭教授《文字学概要》一书,曾在我国的台湾省出版繁体字版,后又被翻译成英文、韩文、日文版,对全球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的人群了解和研究汉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也为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沟通搭起了一座桥梁。
对于裘先生的学术成就,哈佛大学教授米歇尔·皮特曾这样评价道:“权威著作《文字学概要》是对中国早期文字历史和性质的价值无可比拟的考察,精湛丰富,而且涉及早期文字很多不同来源的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著作标志着这个领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著名古文字学家、吉林大学教授姚孝遂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字学史》中,同样给予裘先生的学术成果以高度评价:“建国以来在甲骨文字考释上成就最大的是裘锡圭,”他“学风严谨、踏实,研究方法科学周密,研究范围涵盖面广,研究深度令人叹服,其所写的古文字考释文章,精彩纷呈,很少出现问题。考释命中率很高,很多文章都可作为考释古文字的范文来读。”
学术贡献奖的价值,还鲜明地体现在对影响甚大的流行观点的纠偏上。
上世纪80年代起,儒学的“文化断裂论”在西方学术界盛行,人们把中国古代文化在当代的断裂看作中国社会弊端的根源,由此造成了对中国古代文化不合实际的过高评价,人们甚至弃其精华,取其糟粕,并且对中国现代文学加以无端贬责。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章培恒教授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探讨并阐明其与现代文学的内在必然联系,以此来反对这种“文化断裂论”。章先生自2001年起作为主要主持人联合召开了四次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讨会、推出相关论文集,阐发了中国现代文学正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重要观点。参加研讨会的中外著名专家数百人,最终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在社会思潮的变迁中始终坚持真理,是提出卓有建树学术观点的保证。
袁恩桢研究员在《双重运行机制论》一书中提出的独特观点,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被视为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制高点,他的《社会必要产品论》更是获得了全国首届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著作奖。他的《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一书,被认为是学术界研究温州经济的重要起点,他本人也因此赢得了“温州模式创始人”的美誉。
坚持真理,才是对学术高度负责的态度。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研究员回忆道,作为国内第一本研究“温州模式”的专著,袁恩桢先生的《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一书不仅对此后掀起温州研究热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为解除当时“温州模式”所承受的社会压力,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难能可贵的是,三位著名学者尽管年事已高,他们惦记最多的,依然是自己的专业,依然是学术和学术界的年轻人。面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没有到位,袁恩桢先生提出:“我们经济理论界在这方面要大声疾呼,呼吁我们的政策可以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发展,这也是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为上海的发展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裘锡圭先生不忘勉励学术后来者,在他看来,“年轻人精力旺盛,记忆力好,接受新事物快,是做学问的最好时机,也是一个人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只要能够抓紧时间认认真真潜心向学,年轻人一定能够做出比我们这一代好得多的成绩来。”
学术贡献奖,为后来者和整个学术界树立了道德文章的标竿。“学术至大、天下为怀”的理念,更是推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上海学人追索真理、无私奉献。
在他们当中,上海“社科新人”的整体亮相,为上海哲学社科界增添了一抹亮色。作为上海社科界学术新人的代表,徐英瑾、瞿骏、陆铭、苏长和、罗培新、万勇、文军、刘志荣、宋丽娟9位年轻学子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富有创新,人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未来与希望。
薪火相传的上海学术界,在新世纪续写着全新的篇章。
(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时代》栏目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汇报》 日期:2010年12月9日 版次:12 作者:田晓玲
网络版链接:http://whb.news365.com.cn/ly/201012/t20101209_2901461.htm
PDF版链接:http://pdf.news365.com.cn/whpdf/20101209/WH1012091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