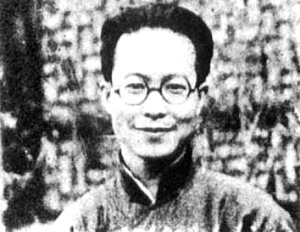
沈从文也曾是亭子间作家
唐小兵
《申报》记载,1930年代上海的亭子间是龟棚式或称火柴匣式的住屋,没有新鲜的空气和暖的阳光,起居饮食,厨灶便桶,多挤在寸金范围区内,楚河汉界,不容越雷池一步。天气炎热时,亭子间热得和蒸笼火炕一样,汗气四溢,臭虫结队。租房者无法,就群向露天大旅社投宿,结果,疠疫横生,传染了一屋子的人,不可收拾。
一篇题名为《亭子间作家》的散文也描述了两个亭子间作家的生活空间的逼仄:“像鸽子笼似的,房子的幅面,不够五尺宽,放着两张床,两张写字台,所有的地方就几乎被占光,来访的客人要是在三五个的话,简直便连驻足的空儿也没有了,在冰冻的冬天里倒容易过去,但是一到了炎炎的暑天,日子可就难挨了。”该文作者对于亭子间作家除了同情之外,也有一些指责,这种指责倒是让我们注意到了某些文人哭穷的另一面:“一辈子就永远踞蹐在亭子间里边活受罪,有时想了起来也会不自禁地觉得悲哀,而这悲哀的延续往往是非常短促的,一下子又忘记了。其实他们两个每一个的入息并不算小,要租那种较舒适的房子自然不是无办法。但是从来都是这样:钱一得到手,镇日价便到外头吊儿郎当,喝酒,跳舞,咖啡座,尽情地纵乐着,轻轻地不上几日的工夫,就把整个月辛苦得来的收获花个干干净净了。”更多的文人并没有这样的潇洒时刻,他们局促在亭子间枯坐半日,没有写作的灵感,或者即使好不容易写了出来,投寄出去,眼巴巴地盼望稿费,得到的却是退回来的稿子,这时还得面对房东时时的白眼和恶狠狠的催交房租。
生活贫困化导致的结果就可能是“牢骚”,牢骚其实也就是变相的公开诉苦。周本斋在《文人与穷》一文里说:“因穷达的不同,文学也呈异观。达者的文学,是歌颂文学。穷者的文学,是牢骚文学。”这种两分法略显简单化,但是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在一个人治社会里,文学者的“达”往往意味着他对权力者歌功颂德,将独立人格折算成个人利益,而穷者陷入生活之困顿,常有怀才不遇之感慨,故牢骚满腹。文人自然靠写稿谋生,可当时的稿费似无法应付生活所必需。
其时《申报·谈言》一篇评论的作者感慨地说道:“在这年头,除了极少数有特殊的地位的作家,每月所入足以应付衣食住之外;其他的一切握笔杆者,差不多都在过着支离破碎的生活,终日咬着牙根与穷鬼周旋,间亦有聪明能干的改途易辙,或奔赴宦海,不过那是少之又少。而别无旁路可走的就只有埋头硬干,以至于贫死、饿死、病死为止。”鲁迅大概在这位作者所说的“少数有特殊的地位的作家”之列,故鲁迅能够经常呼朋唤友去看电影、喝茶,而在上海左翼文人聚会的圈子里,也经常是他买单,这都是有他足够的稿费收入做保障的。
另外一个文人则算了一笔具体的账:“卖文是很不容易的:呕尽心血,绞尽脑汁,写出五六百字,做成一篇文章,还要预付二分没有还价把握的邮花,才能寄到报馆。可是编辑先生与你有缘与否?还是一个问题。即是抱了最大的希望,刊了出来,酬金至多也不过一元至两元之数,但这一元至两元酬金的代价,不知亏损我的心血多少呢!这还算好,有时做一篇文章,语气必定要激烈一点,否则获不到编辑先生的同情,但政府里的大人们,偏偏不原谅你,说你是××派,当即派几个侦探来监视你,把你包围,使你有行不得之叹!运气不济,有尝铁窗风味的危险。”文人得在编辑的尺度与政府的言论尺度之间拿捏分寸,稍不小心就可能以言获罪。除了这种政治性的言论要求之外,各种报刊也有不同的用稿标准,文人得学会写不同风格的文章以顺应买方的需求,精神性的文字也某种程度上商品化了,“但是,一个文人一变而为百货店,确是不易。有的刊物要幽默,有的要礼拜六派或蝴蝶鸳鸯,有的要不反动,而有的不正动。因此,文人要迎合各种市场的需要,确是不可能的事。”
政治规训和商业压迫,这两个外在的因素,自然直接限制了文人的自由表达,很多文人感觉自己不是在写作,而是在出卖灵魂。《申报·自由谈》上的一篇文人内心独白很是震撼人心:“为了生活,我拍卖了我的灵魂,为了生活,我拍卖了我的青春。我吃自己的脑汁,嚼自己的灵魂,是苦?是涩?也只有自己才知道。天啊,这是生活吗?这样,我所以每一看见笔,便存着敌意,便想逃,然而,直到现在我每天还是得寻找我的笔,握着,紧紧地。我想,总有一天我得搁下这劳什子,总有一天我得把我的灵魂叫回来。”这种认同的困境几乎是那个时代的上海文人的普遍意识,这样的认同困境对于上海文人的言论自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亭子间文人的生活世界,无疑是局促在一种物质上的巨大压迫与精神的深度压抑之间。除非有强大的内心世界,这样穷困潦倒的生活,自然会逐渐掏空文人所有的浪漫与激情,只剩下在字里行间虚构性的浪漫意识与批判精神,底里却是穷酸气煎熬出来的自轻自贱与自恋自傲杂交出的“戾气”。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又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劝导其门人都要像弟子颜回那样安贫乐道,坚守一个纯粹的精神世界。这在小国寡民的农业社会里或许不难做到,可在“居上海,大不易”的现代大都市,衣食住行都需要按月甚至逐日计费的时代,贫困往往成为气节的杀手锏,而亭子间常成为埋葬文人理想的坟墓。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东方早报》 日期:2011年6月16日 版次:B10 作者:唐小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