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城市深刻影响了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机制。正是城市,推动了传统文学中雅俗区分的解体,促生了一种兼容文字和视觉图像等多种媒介的综合性“文学文化”的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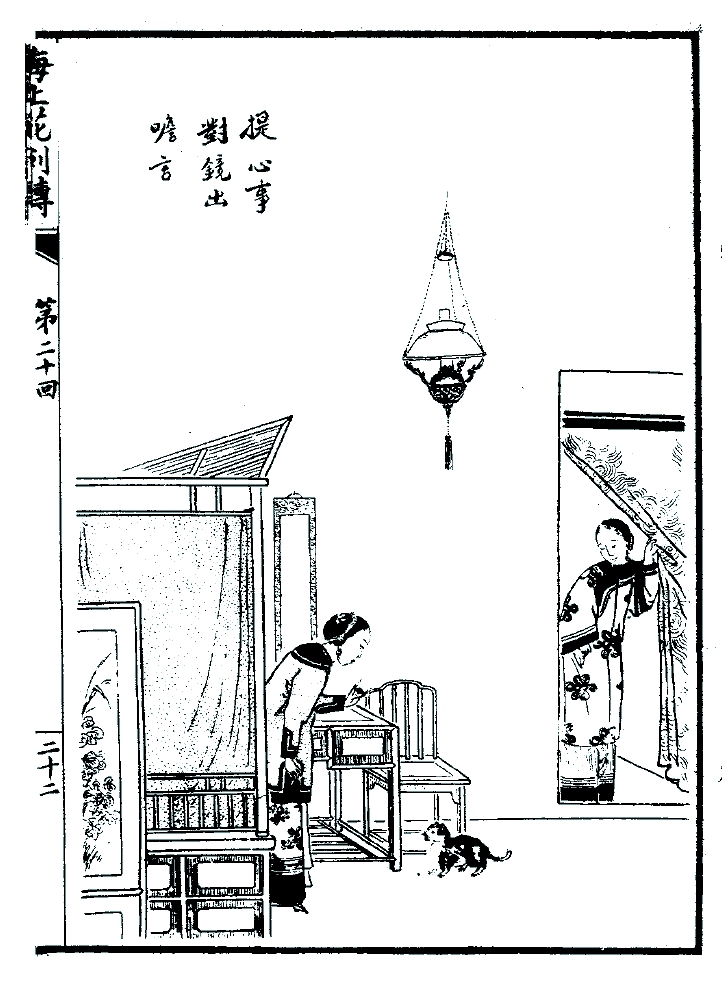
《海上奇书》1892年10期连载《海上花列传》第十九、二十回 资料图片
就报刊媒介而言,近代出版业取代了传统的私人书坊,文学载体从图书转变(或部分转变)为报刊,文学/文化市场形成,不仅改变了文学观念,也影响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出版机构采用新式印刷技术,降低了成本,加快了出版速度。尤其是照相石印技术的传入,实现了对图文原本的机械复制,在传统典籍、通俗文学、报纸杂志、金石书画的出版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1867年在上海成立的土山湾印书馆在光绪初年就掌握了照相石印术。1878年英国商人美查购买石版印刷机,创办点石斋书局,出版了大量照相石印的书籍和图像复制品,1884年创刊的《点石斋画报》就是石印本。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上海的石印出版机构有188家,以国人自办的书局居多。而出版领域的最大变化就是报刊大量涌现,既开创了城市的公共领域,又推动城市文艺和文化生产进入“全球想象图景”。
报刊杂志主导了近代文学的潮流
报刊与近代文学关系密切,体现在报刊汇集了文士,提供了主要的发表渠道。而且,报纸的文学副刊或专门文学杂志主导了文学的潮流。1872年,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申报》创办伊始就在新闻传播这一主业之外,拓展了“文艺专刊”,包括《瀛寰琐纪》《四溟琐纪》和《寰宇琐纪》等,还出版了《申报》馆丛书。近代第一部翻译小说《昕夕闲谈》1873至1875年在《瀛寰琐纪》上连载,译者蠡勺居士就是申报馆首任主笔蒋其章。
《申报》的编辑和作者主要是上海及周边的江南文士,他们发表的诗文小说往往具有写实倾向和时代特点,为日新月异的城市生活留下记录。1911年,《申报》副刊《自由谈》创立,其“游戏文章”有效发挥了社会批评功能,同公众分享某种价值和情绪,切入都市文化机制。1913年,在清末新闻和小说领域都有很大贡献的陈景韩也加入《申报》担任主笔。《申报》通过发表文学创作、出版文学读物,将文士组织起来,形成了一种以“文学”为中心的新的关系形态。
1904年,狄楚青在上海创办《时报》,主笔陈景韩在报纸上开辟“时评”专栏的同时,积极推动小说创作。1914至1918年,包天笑又主编《时报》的《余兴》副刊,“凡种种滑稽游戏、雅俗共赏、趣味丰富之件,为本部所专掌”,集中呈现新闻以外的文艺作品。另一家大报、创办于1893年的《新闻报》,在清末也设文艺副刊《庄谐丛录》,由南社成员张丹斧编辑,主要刊登南社诗词与笑料。1914年严独鹤将之改为《快活林》,除连载小说以外,设有“谐薮”“笔记”等栏目。
此外,近代上海还诞生了很多小报。比如,李伯元于1897年办的《游戏报》,“或托诸寓言,或涉诸讽咏,无非欲唤醒痴愚,破除烦恼”,被称为“小报始祖”。范伯群认为:“以《游戏报》为代表的小报群是通向谴责小说的一座引桥。”
作为一种文化商品的小说
在清末民初,共出现了两次文学期刊的热潮。第一次大致在1902至1907年,且尤为重视刊载小说。这种繁盛与其说是受到清末梁启超等人“新小说”理论倡导的影响,不如说是得到了报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的鼎力支持,而它们这么做,正是因为看到了城市中市民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需要。
读者阅读小说可能是出于获取新知、安顿情感、感受时尚、追求城市生活或单纯消闲娱乐等多种目的,在城市中,小说已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文化商品。近代小说家往往作品多,小说篇幅大、题材集中、故事雷同,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同时,小说也呈现出一种媒介性和综合性。比如,《海上花列传》“穿插藏闪”的叙事笔法,与小说最初在《海上奇书》上连载这一刊载形式有一定关系,更与报刊连载带来的“共时性”和“打断”的阅读习惯相适应,而“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也或许得益于小说对城市经验采用了一种“照相写实主义”。《海上尘天影》在讲言情故事的同时宣传新知,频繁出现知识文本的段落,具有某种“百科全书”性质,就表明在写作上遵循一种媒介的逻辑。
梁启超曾反思报章体例对小说创作的影响:“一部小说数十回,其全体结构,首尾相应,煞费苦心,故前此作者,往往几经易稿,始得一称意之作。今依报章体例,月出一回,无从颠倒损益,艰于出色。”这是从限制的角度指明连载对文本质量的影响,但版面字数、悬念要求等也会促使作者寻找新的叙事技术。报刊连载形式以及时效性讲求,又有助于引起关注,“时效性与‘当下言说’的市民文化心理需求的契合,成就了书局和报馆对利益的最大化诉求”,促进流行文本的生成。
稿酬制度与职业化作家
就文学主体而言,城市推动了职业化作家的产生,越来越多以文学写作为业的作者成为最普遍的文学生产者。正如列文森所言,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是一种“业余文化”的典范,“学者纯文学式的教养是一种与他因此而有资格处理的公务相分离的学问”。也就是说,文学阅读和写作主要是作为教养和兴趣,而不是一种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行为。但近代以来首先在通商口岸城市里,出现了最早一批职业化作家。他们游离于科举之外,与西人合作,进入书局(如墨海书局)译介西书、钻研格致之学,或者进入报馆担任编辑、主笔或记者。
1875年,申报馆开始招聘专职记者,并承诺“薪金”“从丰酌送”,一种新职业开始浮现。同样从这一年开始,申报馆首次向文人征求小说排印售卖。稿酬制度有效保障了作家权益,推动了小说兴盛。梁启超的《新小说》杂志明确公布了稿酬标准,创作每千字从4元到1元5角四等,翻译每千字从2元5角到1元2角三等。报馆在拓展挣钱的门路,也为文人创造种种新的可能。这批新式文人擅长跨文体写作,往往兼及笔记、小说、报章评论等。
而在科举废除之后,以写作和翻译作为城市里新的谋生之道的文人就更多了。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著作权律》,稿费和版权得到法律保护,这更保障了职业作家的生存。《小说月报》创刊时,“征文条例”中规定了四等稿酬:“甲等每千字五银元,乙等每千字四银元,丙等每千字三银元,丁等每千字两银元。”林纾翻译小说,商务印书馆的稿酬也是每千字五元。周瘦鹃家境贫寒,1911年他的剧本《爱之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后,得到14块大洋,全家为之欣喜。稿酬制度至民初趋于稳定。稿酬既提供了保障,同时也使得作家和编辑更加受限于出版商。简言之,他们在商业机制中重塑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文学主体的另一个变化是,文学创作和接受不再局限于作家和读者,编辑、出版商对文学有了深刻的介入和干预。前文提到报刊连载小说,连载为作者和读者的互动提供了可能,小说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可能就要考虑读者阅读趣味和接受程度,做出种种调整。
传统的诗文高高在上的地位被颠覆了
就文类秩序而言,城市促进了文类秩序的更新。传统的诗文高高在上的地位被颠覆了,小说戏曲的价值得到空前地肯定。文章不再谨守唐宋古文或八股时文的藩篱,像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打破了古文定式,引入新名词和新文法,条理清楚、感情充沛,或如陈景韩开创的随事赋形的“时评”体,在读书人中相当风行。在小说类型上,谴责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狎邪小说、言情小说等都比较繁盛。这既与城市生活现实的刺激有关——这些小说表征了当时城市市民在政治、科学、正义、情感等方面的想象与焦虑;也是全球文学流动的结果——翻译文学的选择成为作家创作追慕的对象和资源。
谴责文学不仅批判荒唐的世道,而且以一种对丑怪的耽溺表达出怀疑与虚无。科幻小说杂糅古今中外的科学与神话,畅想坐气球开拓月球殖民地或是运用电能改造社会、建立大同世界。侦探小说重在正义担当,“福尔摩斯探案”系列或“亚森罗苹”系列的翻译,程小青“霍桑探案”系列的创作,既是对城市生活的匿名性和风险性的揭示,又表现了通过知识占有和逻辑推理完成对城市的重新掌控和秩序感的重建。狎邪小说引领读者深入城市欲望世界,彰显城市如何发挥着核心作用。诚如王德威所言:“韩邦庆只有在呼唤这个城市(指上海——引者注)魔幻似的名字时,才能启动他笔下爱与欲的传奇。”言情小说则聚焦城市青年在爱情和婚姻上的浪漫与哀愁,精准握住了新旧嬗变之际个性解放与束缚的冲突,打造了一个“感伤的共同体”。这些流行的小说文类体现出现代城市生活经验与感觉的某种赋形。而出版机构的策划和运作则加剧了特定小说类型的生产与传播。
在戏曲戏剧领域,上海在近代戏曲革新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04年陈去病、汪笑侬在上海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倡导戏曲改良。1904年汪笑侬在春仙茶园上演《瓜种兰因》,以波兰亡国历史为背景,影射晚清中国社会危机。这是京剧舞台上第一个“洋装新戏”。1908年新式剧场新舞台落成,采用镜框式舞台,演出了《新茶花》《黑籍冤魂》等,开启了海派京剧之先声。
海派京剧重视舞台设计、灯光和服装,突出视觉效果。民国初年梅兰芳来上海后,深深意识到“上海舞台上的一切,都在进化,已经开始冲着新的方向迈步朝前走了”。回到北京不久,他就启动了新戏的编演。特别是排演时装新戏,就是向海派京剧的方向靠拢。1920年,梅兰芳在上海走上银幕,由商务印书馆影戏部拍摄了《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的戏曲影片。《新茶花》《黑籍冤魂》的图画在1909年《图画日报》上刊载,被冠以“世界新剧”之号,“新剧”之名由此为大众所知。与此前由上海圣约翰书院演出的《官场丑史》一类“学生戏一起”,共同成为“新剧”的源头。进入民国,新剧再度兴盛,剧本主要靠翻译国外戏剧和小说改编,而改编多来自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新剧家和通俗小说家合作日渐密切。同时,新民社与美国亚细亚影戏公司合作,把文明戏《难夫难妻》拍成电影。1914年民鸣社办的《新剧杂志》问世,综合性文艺刊物也常有关于戏曲的评论。可见,戏曲戏剧与小说、电影密切互动,并借杂志平台扩大影响,这种媒介融合凸显出城市消费文化进一步拓宽了文学的边界。
阅读原文
作者丨张春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来源丨文汇报
编辑丨王蓝萱
编审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