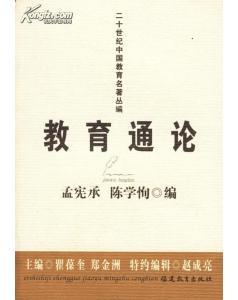 进入新世纪以来,“回顾”和“反思”俨然成了我国社科界的“主旋律”,作为社会科学的一支,教育学也莫能外。与其他有关中国教育学科的世纪反思不同,华东师范大学瞿葆奎教授和郑金洲教授担纲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第一辑,50本,共69册)(以下简称《丛编》),将审视历史的权利交给读者,让读者在与原典的直接对话中,洞察那个时代教育学科走过的艰难历程,感悟那个时代教育学者彰显的学术风采。
进入新世纪以来,“回顾”和“反思”俨然成了我国社科界的“主旋律”,作为社会科学的一支,教育学也莫能外。与其他有关中国教育学科的世纪反思不同,华东师范大学瞿葆奎教授和郑金洲教授担纲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第一辑,50本,共69册)(以下简称《丛编》),将审视历史的权利交给读者,让读者在与原典的直接对话中,洞察那个时代教育学科走过的艰难历程,感悟那个时代教育学者彰显的学术风采。
这套《丛编》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从2004年4月启动,到2010年底方才告竣,其间汇集了一大批老、中、青教育学者参与编校。其所选辑的主要是20世纪上半期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领学科风骚的教育著作。它们都是经过一定的时间检验,展现出独特的学科价值,或在当时、或在当下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或实践影响。
概括来说,这套《丛书》的意义不仅仅是简单地整理和挖掘“国故”,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整理和挖掘,追溯中国教育学科的百年谱系,重温中西教育思想的血脉,接续断裂的教育学术传统。
追溯教育学科谱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师范教育的出现,教育学开始中介日本进入中国。大体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从最初的译介,到改编,再到自主的撰述,中国教育学蔚为大观,分支学科不断涌现,并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鉴于这些教育著述多是以知识体系或主题领域为主导的,《丛编》不打算(实际上也不可能)包罗万象,而是聚焦在“领一定学科风骚”的著作上。因此,这套《丛编》总体来说是20世纪上半期教育学科发展的剪影。
首先,收入《丛编》的部分著作,本身就是中国教育学及其分支领域的发轫之作。继译述日本立花铣三郎《教育学》(1901年)之后,王国维在1905年又编写了《教育学》一书。前者是国人翻译的第一本完整的教育学,后者是国人编著的第一本教育学。这两本开中国教育学风气之先的著作,赫然位列《丛编》书目的“榜首”。
其次,《丛编》反映了当时教育学科发展的基本格局。20世纪初叶,随着西方“教育科学化”运动的展开,教育学在与心理学、伦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的双向渗透中,衍生出一批交叉性或边缘性的教育学科分支。大抵在1920年及稍后,这些分支先后在中国以不同方式“登陆”。《丛编》基本覆盖了这一时期“登陆”的教育学科分支(包括课程论与教学论),同时折射出这些分支在当时的成熟程度和地位格局。
再次,《丛编》呈现了教育学及其分支的体系多样性。对于那些在当时发展相对较快的学科领域,《丛编》通常选择多本在体系上具有一定代表性或独特性的著作。例如,在教育学方面,张子和的《大教育学》主要属于赫尔巴特教育学的传统,以教授为重心;孟宪承的《教育概论》和吴俊升的《教育概论》主要受杜威教育学的影响,以儿童的发展为起点;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和钱亦石的《现代教育原理》主要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些选择,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丛编》主编的匠心。
重温教育思想血脉
如果学科体系是骨架的话,那么学说或思想就是血脉。西学东渐,带来的不仅仅是崭新的学术架构,而且从更深层来说是中西思想和文化的激荡。学科体系是“硬的”、“形式性的”,可以通过建制予以迁移,但是学说或思想是“软的”、“实质性的”,要从它赖以生成的“旧土”移居它全然陌生的“新地”,必然需要一番适应和改造的功夫,否则就会出现“南橘北枳”的后果。
在这套《丛编》中,您可以看到,早期教育学者既表现出对西方教育思想或学说的广泛借鉴和吸收,同时面对这些思想或学说的冲击,又表现出对本土的教育传统和现实的深重关切。他们对于外来的教育思想或学说,已经开始在“照着讲”的基础上注意“接着讲”了;不是简单地“盲从”或“迷信”这些思想或学说,而是在“同情式理解”的基础上有所综合,有所批判,甚至结合本土的传统有所创造了。例如,吴俊升就明确说,自己“仅为杜威学说之研究者,而非其追随者”。
在这一时期,许多学者都逐渐萌生了一种明确的“中国意识”,开始考虑在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下,如何立足中国自身独特的环境,使西方的教育思想或学说更贴近中国教育实践,并裨益于中国教育实践。他们感到,“教育学有共同之原理,亦有本国之国粹”,因而不能简单地移植或照搬外来的教育理论,而必须对这些“舶来品”保持一种“警觉”。他们希望通过对西方教育理论的引进和介绍,但同时也在探索就如何立足中国本土,实现学科发展的“中国化”。例如,萧孝嵘曾在其《教育心理学》中指出“我国人的心理背景与他国人的心理背景自有一些差别,故在有些事件中,不能根据国外之研究结果推知本国的情形。本书为顾及此种特殊背景起见,尽量采用我国的研究资料。在某些问题上,如无本国的资料,或有之而在某些方面尚有问题,则采用国外的资料”。
接续教育学术传统
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教育学科是在中断传统学术的基础上起步的,又是随着政制的更替在“推倒重来”中前行的。新中国成立之后,20世纪上半期已经初具形态的教育学科接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改造。在“以俄为师”、“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号召下,这种改造逐渐演变成按照苏联教育学科体系加以规划。中国的教育学科只开一扇“北门”,在数量上大为收缩,仅留下了教育学、心理学、各科教学法、教育史等学科;在内容上倒向了苏联教育学者的研究成果,禁闭或批判了西方学者的教育理论。中国教育学科经历了一次“血透”。“引进”又一次成了教育学科建设的主题,而重点在译介苏联的“教育学”教材。虽逐渐有些结合中国实际的自编教育学科教材,但框架上,甚至内容上基本是苏联教育学科的“复制”。即便是在1949年-1966年间形成的有限的学科建设成果,也随着“文革”的到来,迅速淹没在一统的“语录化”教育表述之中。
经历了30年的曲折或中断,我国教育学科又重新走向开放,放眼欧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在追逐西方的过程中,今天的许多教育学者以断裂的眼光审视历史,轻视甚至忽略20世纪上半期我国教育学科所积累的丰富成果及其沉淀的厚重精神,从而遗失了滋养当代中国教育学术的一个重要源泉。有鉴于此,《丛编》希望通过这些闪耀思想光芒的著作,重塑厚重的历史意识,接续失落的学术传统。
《丛编》的意义,庶几在此?
《福建日报》 日期:2013年5月10日 版次:11 作者:沈群
链接:http://fjrb.fjsen.com/fjrb/html/2013-05/10/content_40903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