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是一本全方位呈现中国当代艺术面貌的艺术辑刊,通过多棱镜般对古今、中西丰富多彩的艺术与哲学现象的折射,旨在呈现中国当代艺术的面貌、进展和方向,切实推动当代艺术的理论研究和学术评论,有效激发中国当代艺术的真正本土化与国际化。

《作品A》,作者井上有一,1956年。 书中插图
《现象》(第一卷)出版后,以“艺术·思想·文化”为主题,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与巽汇XUNWAY共同主办了一场研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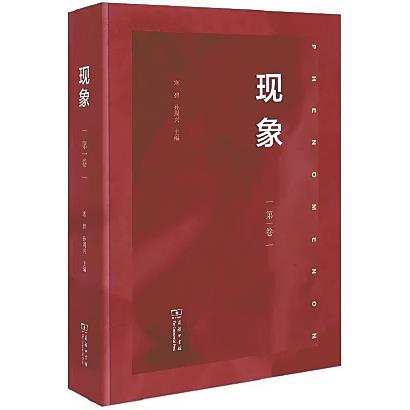
《现象》 (第一卷)寒碧 孙周兴主编 商务印书馆
一本偏离艺术的艺术辑刊
寒碧(《诗书画》杂志原主编,现为巽汇XUNWAY总策划,《现象》辑刊主编之一):《现象》是一种关于当代艺术、当代哲学、当代思想文化史学的创作与研究刊物,我从四个方面简要阐述办刊初心。
一是《现象》以做艺术尤其当代艺术为初意,不过在编辑过程中感到问题稍复杂,中国当代艺术40年间虽然也有一些成绩,但在全球化这个总场域里,依然居于边缘,太多流于追随,无多原创力量,包括感受力量、思想力量、文运力量等。这些方面应该作为问题研究的方向。
二是对当代艺术的研究,要摆脱格式化的陈词滥调,思想界和艺术界两者目前也不是完全没有交集,只是互相找不到对方典要。
三是关于当代艺术、当代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前者是个体非法不纲,后者是整体秩序规定,我希望在这种间距关系里看到真正的创造。
四是在艺术创作和研究中,其前提不是解释和证明“传统”和“西方”的一种修辞或者美化,更不是生吞活剥、生搬硬套,也不是观念优先、主题先行,而是生活感受、思想活力、学问商量。
因此之故,才有《现象》。正如陈散原诗,“此意深微俟知者,若论新旧转茫然”。
孙周兴(浙江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美术学院讲座教授,《现象》辑刊主编之一):当代艺术与20世纪的人文学特别是现象学紧密相关,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不会产生如此结果。当然还有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尤其是技术,诸要素促成了当代艺术的发展。但是,如果不是人文学或者现象学的思潮激荡,“二战”以后当代艺术的出现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寒碧兄一直想把《现象》做成人文学的辑刊,乃至稍稍偏离了做当代艺术的初衷。
另外,他认为人文科学整体要有一个新的使命,推动当代艺术和艺术哲学的发展。
爱美和爱智慧原本是同在的
张文江(同济大学人文学教授):《现象》体现了两位主编对学术的认知、对未来的想象:当代艺术和思想文化史学,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现象》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根据胡塞尔的说法,一个是现象是“什么”,一个是现象会“如何”。“什么”大致可以对应西方文化的两方面,一方面是逻各斯,一方面是密索斯。前者的背后是哲学;后者的背后是宗教,包括艺术。当下,哲学和艺术好像变成了两条路,但从源头来讲,它们原本是一条路。比如,在《会饮》和《斐多》里,爱美和爱智慧是同在的。然而后来,我们把爱美扔掉了,爱智慧则变成了形而上学。这样是会有问题的。《现象》现在在做的,正是要回到传统的路上来,让爱智慧和爱美重新结合在一起。
王广义(艺术家):《现象》建立起了艺术界与思想界对话的桥梁。反观近40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由于缺乏思想界的支撑,在所谓“话语权”这个问题上是缺失的,中国当代艺术仅仅是一种边缘的存在。在国际舞台上虽有知名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但在全球范围内的当代文化之中,不过是一种“特例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他文化”影响的产物,不具主体性。
艺术家应当有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表达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不论这种问题是关于文化的、经济的、历史的,还是种族的、信仰的。因而,我们也特别需要与思想家们有互相观望的平台。事实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心目中的当代艺术,也就是一种写作。
严善錞(艺术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当代美术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艺术家们的跨界思考。那一时期,文学、哲学与美术的关系非常密切,互相交流,互相参与。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王广义讲的思想与艺术的互动本来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二是因为我们当时的知识过度贫乏,所以也有一种求知或者说好奇的心理在起作用。
我很难说清楚知识或者说思想观念对于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有多少实际的作用,或者说如何起作用。我想大概有这么两种可能性:一是所谓的变化气质,尤其是诗歌和文学,它能启发画家们如何打开自己的感觉,去感受自然。二是改变观念,这在当代艺术中尤其显著,从杜尚到博伊斯,他们不仅是艺术家,也可以说是思想家。
章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今天,我们对于很多艺术现象的追踪,都是追踪到西方那个源头。很少有艺术家在谈中国的背景或者中国的源头问题。这本身构成了我们今天非常值得面对和重视的问题。说到底,这仍然是学科化带来的后果。
彭小瑜(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对现象的观照意味着,艺术不再为艺术而艺术,哲学不再为哲学而哲学,二者都必须具有行动力,都应该致力于让生活更加美好和完满。李公明先生在讨论施密特和诺尔德艺术—政治经验的文章中写道,“杰出的艺术家必然具有对人性的深刻理解。”《现象》中的很多文章,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和思想深度,同时经由委婉的文字和平静的表述,自然充溢着从容不迫、温暖和温润。
让更年轻的朋友加入进来
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提两个建议。
第一,要考虑聚拢性效应,要有一个明晰化的处理,让这个时代的读者找到它,而不能做成只是在熟人文化圈里流转的刊物。
第二,要聚焦新的现象。比如今年上半年大火的NFT艺术品交易,是艺术界的大事件。《现象》要重视类似这样的互联网时代对艺术的冲击,要让更年轻的朋友加入进来。
阅读原文
记者丨顾学文
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梁欢
编审丨郭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