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壮大和成熟的关键时期。当时国内外不同人物从不同角度所作的观察和判断,是对中国共产党人优秀政治品格的最好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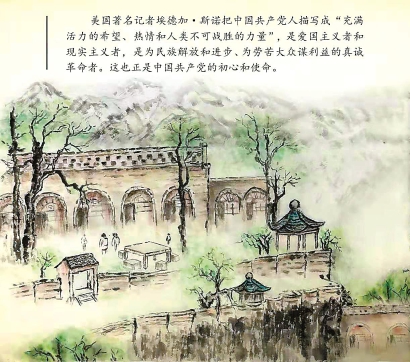
柳友娟 绘
坚定信仰
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信仰历来是真诚的、坚定的。这一点,在华的外国人通过长时间考察后取得了一致认同。
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和红军相处四个月。他把中国共产党人描写成“最自由、最幸福的”,因为他们强烈地相信自己所献身的事业是“完全正义的”。从他们身上,斯诺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信仰坚定,而且还勇于为真理而奋斗、为信仰而战斗。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史沫特莱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认为“没有人比他们更勇于为信仰而献出生命”。记者、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认为,新四军“具有无比英勇的牺牲精神”。
如果说这些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偏于同情的话,那么美国官员也许能够以较为中立的立场来看待问题。1945年2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二秘的雷蒙德·卢登,在晋绥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展开了四个月的旅行。之后,写下三份实地考察报告发给美国军事情报助理参谋长。他在报告中说“每个八路军领导人,无一例外,都是坚韧不拔的、久经考验的志士”,是“最现实、最脚踏实地、最坚强勇敢的群体”。
1943年,徐复观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处联络参谋的身份驻延安半年。他向蒋介石汇报说:尽管国民党中有很多好人,但很难发现真正为实现三民主义而肯作无私努力的人。从这则史料可以反证,中国共产党人是为信仰、为理想而“无私努力”。
抗战时期,中共英勇抗战的名声在国统区也广为流传。重庆的一名高官私下对史沫特莱感叹:“阵亡在前线的共产党党员人数之多真令人惊讶。”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在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看来也是令人肃然敬仰的。
在敌伪军中,也不乏对中国共产党人崇敬有加之人。日军在华北扫荡时曾表示,共产党的干部、士兵“均抱有对主义的信仰和正确的政治态度,民族意识相当高昂”,中共的“战斗意志相当强,特别是在村庄的防御战斗尤其坚强,战斗到最后一人仍然顽抗到底的例子屡见不鲜”。
苏北伪军署长赵简子在给汉奸陈公博的信中,对共产党同样充满佩服。他总结共产党在政治、民运、经济、教育和宣传等方面的特长,并强调共产党“上下没有隔阂,政策贯彻到位,党员刻苦耐劳”,认为值得好好学习。
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呢?斯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是为民族解放和进步、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真诚革命者。换言之,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如何实现这一理想?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方法,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记者冈瑟·斯坦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人坦白地称作中国共产党员理所当然要遵循的‘正确的思想方法’;而马克思主义的简单的要素,以唯物的观点来看待一切社会现象,看来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党员的思想之中,即使受教育很少的党员,也是如此。但是,我并不觉得中国共产党党员是迷信教条的。”
坚决抗日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中国共产党又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先锋队组织,就决定了其抗日必然也最坚决。
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评论:“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日本人有这样的结论,是长期观察的结果,也是久陷中国战争泥潭而不得胜利的最后哀叹。
抗日战争未全面爆发之前,有人就认为中国共产党必定是坚决抗日的。日本有观察者认为,中共从“满洲事变”开始,尤其是1935年的“八一宣言”以来,实行“执拗的对日战争宣言和策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对日态度也是迥然不同的。这一点,从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说:七七事变后,与国民党嫡系中央层对抗战非常悲观不同,中国共产党是要坚决抗战的。
中共为什么会抗战坚决?除了信仰坚定外,还有军事战略的底气。对此,外国记者也好,国民党人和日伪军也罢,都对中共的游击战交口称誉。
抗战期间,国民党也曾考虑过游击战。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会上,他提出“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同时,向中共中央打电报,请求派人前来教学。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一个30多人的代表团,由叶剑英任团长,前来教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的军事名篇,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对其甚为赞赏,认为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方略”。在蒋介石的允许下,《论持久战》得以在全国印刷发行。可见,游击战当时是得到国民党认同的。
外国人对游击战也抱有极大的兴趣。《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不少八路军、新四军在前线抗击日军的新闻和评论,认为中共“游击战非常活跃”、中共军队“是中国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之一”。美国海军陆战队队长卡尔逊在《关于中国西北部军事活动的报告》中说:“八路军的领导人发展了非常有效的游击战模式;日军在应对传统军事战役时效率较高,但面对没有固定章法可循的游击战术却无所适从。”
日军是吃过中共游击战术大亏的。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哀叹,华北敌后战场是谜一样的战场,这里有谜一样的组织、谜一样的军队、谜一样的战役,是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谜。日本少尉二村在书信中写道:“八路军、新四军好像飞舞在饭上的苍蝇一般,你进他就走了,你退他又来追,真是为难得很。简直防不胜防。”
游击战让日军作战望风扑影、劳而无功,日军情报部门亦坦言“对擅长游击战及退避战术的共军,以武装讨伐……收效极微”。这样的持久作战,进一步影响到了日军的士气。1941年,在冀中一带作战的日军骑兵大队长加岛武非常气馁:“旷费时日,真想举手服输。”
坚持民主
除了军事战略和战术层面,中国共产党还始终扶持民生、扶助民主、扶植民力,从人民的拥护中汲取奋斗力量。
尽管战争使得民生受到极大影响,但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方法来减轻人民负担、照顾各阶层利益。美国《时代》周刊驻远东记者白修德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和那些为穷困所迫、深受苦难的农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从那里他们得到最大的支持。
日本驻华北方面军1941年制定的《剿共指南》认为:“中共为了争取农村民众,以便用于抗日战争,积极策划减轻农民历来深以为苦的各种负担,并以此博得农民的信任和欢心。”效果如何呢?一个伪军智囊坦承,中共势力范围内,民众可以安居乐业,不会绑架勒索,不会草菅人命。而在伪军统治区,捐税非常严重,绑架勒索频频,老百姓叫苦连天。
中国共产党还在抗日根据地积极进行民主改革,尤其是在妇女解放上付诸了极大努力。1964年,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工作。一天,在接见上海市部分领导干部时,他握住了孙兰的手,并对其他领导干部介绍:“这是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是我家乡的父母官。”
这位被周总理称为“父母官”的人,在1945年7月至1947年1月间,曾担任淮安正、副县长。那个时候,史沫特莱曾采访过孙兰,称其是“共产党的女才子”和“红色中国的女县长”。
为了带领人民坚持抗战、形成抗日的铜墙铁壁,八路军“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有的一切都主要为战争服务”。日军在清乡失败后曾感叹新四军组织力量强大,认为“新四军之长处,统一民意,导以一定方向,结成有组织之力量”。华中地区的伪军首领亦承认,80%的农民“风起云涌般地环绕在共产党的周围,形成了共产党的坚强组织、普遍而又强而有力的外围组织”。
1938年3月,德国驻华大使馆办公室负责人向柏林发出的报告指出,日军不能控制所占铁道线左右的广大领土,因为有一支独立的中国军队得到了人民的充分支持。
1939年,日本调查机构“兴亚院”在华中地区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新四军维护群众的利益,农民支持新四军。3年后,日本另一家调查机构“满铁上海事务所”对苏北的新四军进行调查后指出,中共努力改善民主的热情,使民众受到感动,因而能取得民众的支持。
日本士兵梅田照文在百团大战中被俘,一度自暴自弃。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接受改造过程中,他耳闻目睹党政军民关系融洽,内心受到极大冲击。后来,他在回忆文章《第二故乡的怀念》中这样写道:“我在这里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得到人民由衷的拥护和支持的情景,并为之深深地感动。同时,也体验到了密切联系群众、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的必要性。”
得民心者得天下。1940年,陈嘉庚先后到访重庆和延安,对比后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1941年6月26日的蒋介石日记记载这样一段话:“阎锡山对其左右明言,以后国民党、共产党与汪伪三方面之成败,共党则为六分之三,汪伪则为六分之二,至国民党则仅有六分之一之希望。”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1944年7月28日的报告中断定,“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占有确定的和重要的地位……在短短的几年中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
阅读原文
作者丨侯艳兴(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郑海容
编审丨戴琪
